《禪與摩托車維修的藝術》:你永遠可以走上「第三條路」
「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得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也許反過來說才成立。
這是一個 Podcast 的筆記,在文字上非常的潦草凌亂,但我還是放上來了,作為一種「收錄」。
全文將近九千字。我已經盡力刪減了(原本當然破萬),但是在刪減的過程,我感受到我想講的東西一點一點地失去,像是越是用力抓住水,水就越是離開你的掌心一樣。
於是只好在九千字停止。,並且根據這篇文的內容,簡單錄一集 90 分鐘的 podcast。
Podcast 的內容跟文字相關,但不太一樣,基本上文字涵蓋的還是比較多一點,但 Podcast 更 Real 一點,看你喜歡哪一種。
Podcast 請聽這邊:
(目前只有 Firstory 的介面可聽,Spotify 與 Apple Podcast 還在處理中)
文字的話,閱讀時間可能要 15 分鐘。
如果你不想讀太長的內容,跳過這篇吧。生命中有多少個 15 分鐘可以浪費呢?
上個月讀到《The Inner Game of Tennis》,幾乎要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這是一本奇書。
這本書最奇妙的事情就是,全書都在講「如何打網球」,但對我來說,這是一本「如何修行」的操作指南。我在這本書裡,學會了兩件最重要的事情:
1. 試圖用「自我一」來掌控自己,不斷告訴自己「肩膀要放鬆」來打球是無效的,你只是徒增困擾,讓身體緊繃;相對的你可以放下「自我一」的掌控欲,單純只是觀察,讓身體本性的「自我二」自由發揮,這時候你會發現身體內在的智慧比你想要掌控的大腦強大太多了。
教練可以在球場裡面自然而然地複製人的本質狀態,讓完全沒運動習慣的大媽在 20 分鐘內學會打網球。
2. 任何已經用語言定義的東西,都是你更難學到的東西,你複雜化了這整件事。相對的,用你的身體自然而然模仿與感受,會有最好的吸收效率。教練的學生觀察之後,唯一沒有學到的東西,就是他用語言表達出來的東西。
這讓我開始想:如果在網球可以這樣做,在音樂、滑雪、工作都可以這樣做(以上都是教練寫的書),那麼,在生活如果也可以這樣做呢?
這一個月,我於是帶著這樣的思考回到台灣,並且在這一個月中,我試著「不做任何事情」,不在我的生活裡加上任何更多新的東西,不多做任何事。
只是單純地觀察,並且一點一點地把多餘的情感上的包袱,多餘內在的爭戰都一點一點解除掉——如葛羅托斯基所說「Via Negativa」的減法哲學。
我不再試圖逼自己日更,不再逼自己工作回信。我只是觀察,在靜坐中,觀察我的呼吸如何潮起潮落,觀察我與內在如何爭戰摔角,觀察我如何與人對話,觀察他人如何存在
這一個月,成為了一場很奇特的旅程。
回台灣這三個禮拜,我每天都約了一個朋友見面,與他吃午餐。我發現這件事,結合「觀察」的練習,竟然成為一場不斷自我掏空,讓他人走進我的身體,在我身體裡面作客的過程。
而這似乎產生了一種「共時性」,在一次又一次的對話中,我所自我爭戰的,我所懷疑的、痛苦的、撕裂自己的、生命無法承受之輕的...這些問題,似乎都得到了某種啟發。
最不可思議的是,即便是我內在最深處的自我懷疑與詰問,竟然也在他人的口裡,親自告訴了我答案。
於是我發現,「觀察」具有一種很特殊的魔力,單單只是觀察身體的一個部位,有時就可以解除掉累積好幾個月的肌肉張力;單單只是觀察一個人如何說話,有時你就會感知到他內在從不敢與他人說的恐懼。
單單只是觀察自己,你就會不斷解構自己。當沒有了自己,你便與身邊的人事物,與這個世界成為一體。
2025 年的最後一個月,是我卡關的一個月,但我也發現,「卡住」是人生最好的祝福,「放棄掌控,單純觀察」則是面對卡住的最好方法。
而也很奇妙地,我這一個月的體悟,竟然與一本書深刻的共鳴,這一集 podcast 我想要介紹這本書:《禪與摩托車維修的藝術》。
▋ 這是一本怎樣的書
《禪與摩托車維修的藝術》是美國作家羅伯特·波西格在1974年寫的一本哲學小說。
故事表面上是在講一個父親帶著兒子騎摩托車橫越美國的旅程,但作者藉著修理摩托車這件事,來探討一個很大的問題:什麼是「質素」?什麼是「好」?
波西格認為,現代社會把理性思考和感性體驗分得太開了。他透過修理摩托車這個過程,想要說明:當你專注地、用心地做一件事情時,不管是修機車還是做其他事,你都能從中體會到某種「質素」。這種品質不只是技術上的好壞,而是一種更深層的東西。
這本書也穿插了作者自己過去的故事,他曾經因為過度追求哲學上的完美而精神崩潰。所以整本書同時在講三件事:一段旅程、一個幽靈、還有對於「禪」的思考——一個美國哲學家,試圖整合西方哲學與東方的禪修傳統,在摩托車旅行的框架下討論這件事。
這一集 podcast 不會單純講書裡面的內容,而是用我這一個月「放下試圖掌控的自己」,來幫這本書做一種「註解」。
▋ 究竟,什麼是「文學」?什麼是「藝術」?
在台灣三周,我到台南與高雄閒逛了兩三天,也是見南部高雄喜劇開港的朋友們。
在台南我逛了台灣文學博物館,當時恰巧有一個旅行文學的特展,開頭是舒國治的遙遠的他方,或者林獻堂環遊世界的皮箱,那些唯美的文字;然後結尾,竟然是旅遊 Vlogger 的 YouTube 影片,在吃府城豆花。「豆花好吃,這間我還會再來...」
這對我衝擊太大了,我不斷地在想:旅遊 Vlogger 也算文學?那究竟什麼叫做文學,什麼不叫做文學?黃山料是文學家嗎?我平常在臉書上寫的那些文章,也算是「文學」麼?
假設是,那幾乎就能推出「萬物皆文學」的結論,那麼,文學博物館、文學系、文學理論研究有什麼存在的必要?
假設不是,那文學與否的邊界究竟在哪裡?難不成又只是學院裡面的教授說了算,我服從於所謂的「學術權威」?憑什麼?
這點也可以延伸到不同領域:什麼叫做「喜劇演員」?喜劇演員跟好笑的人有什麼不一樣?
什麼叫做「藝術」?憑什麼你畫的東西可以放在高雄美術館裡面,我畫的東西只能進垃圾桶?難道只是因為你讀過法國巴黎美術學院?
我們先撇除實務上台灣藝評界與觀眾的鑑賞能力問題,至少在理論空間裡,我發現有一種對張存在,一邊是「文學理論研究」,告訴你怎樣的典範是文學;另一邊是「萬物皆文學」的浪漫感知論,只要你有 fu,這就是文學。
問題是,答案肯定不在任何一個極端裡面。
完全理論研究派,那你的文學就是狹隘的;完全「萬物皆文學」派,那黃山料也是文學,我傳的賴訊息也是文學,那「文學」這個字根本沒有意義了。
任何一個極端,都只是我們在語言中自己發明的概念,也就是意識形態。意識形態不是答案,只是一種方便溝通的工具。
我相信答案不在任何一邊,而是在這兩者的「張力」之中。
▋ 古典與浪漫/絕對與相對/太陽神與酒神/理組與文組
一邊是「只有藝術理論佐證的才叫藝術」,我稱之為「藝術絕對主義」
另一邊是「只要有 fu 的就叫做藝術」,我稱之為「藝術相對主義」
這個兩個極端對坐,產生的「張力」,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這個概念也是《禪與摩托車維修的藝術》這本書,作者想要討論的重要主題。
作者提出兩種看待世界的方法:「古典理性」與「浪漫感性」。
古典理性強調拆解、邏輯、分析,要找到事物表層現象之下的「底層邏輯」,在歐洲傳統裡跟「父權、男性、陽剛氣息」相關,在台灣最接近的概念就是「理組」。
浪漫感性則強調表層現象,直覺感受式的認識,直觀地存在,在歐洲傳統裡跟「女性、陰柔氣息」相關,在台灣最接近的是「文組」。
作者為何使用摩托車當作案例?因為摩托車可以很好象徵兩種氣息。在摩托車騎乘上有「浪漫感性」的自由奔馳,也有「古典理性」的逆操舵、姿勢技巧。
摩托車維修,表面上看是完全的「古典理性」,但是對於一個熟悉機械的人來說,摩托車維修在在有「浪漫感性」的,無法用邏輯與理性解釋的直接認識面。
現代社會的問題,從 1970 年代這本書出版的時空背景開始,即是「古典理性派/浪漫感性派」之間的對立與分裂。「科技人/工程師」不懂得什麼叫做生活,「藝術家/詩人」不懂什麼叫商業。
這個分裂在台灣尤其危險。大多數討論 AI 的古典理性派,面對 AI 帶來的哲學問題回應皆凡善可陳,僅止於「AI 很厲害,所以獨立思考很重要...」;浪漫感性派則一昧反對 AI,拒絕理解背後的原理與技術。
但現在生成式 AI 的科技之力已經「越界」到藝術領域,把浪漫感性也拆解成無情的數學編碼了——科技早已經吞噬了一邊,從 1974 年美國的思潮來到今天已經在改變了,我們的思想卻還停留在原始的「理組/文組」這樣的分裂對立之中。
我們需要解決這樣的分裂,在對立之中找到出路。
我們需要「第三條路」。
▋ 與天使摔角:在張力中,你才看得見第三條路。
在《禪》這本書作者思想中,兩個極端誕生之前,先有一個東西叫做「質素」(Quality),這兩個極端的對立是因為 Quality 才誕生,是人類認識 Quality 的兩種取徑。
答案不在極端之中,而是在對張中,在自我辯證的過程中,不斷接近真實。
在兩個極端對坐的張力下,身體是痛苦的,你會面對苦難、爭戰。
我時常感受到我的身體裡有這樣的爭鬥。一邊的我是古典理性代表,告訴我要努力,要做好課程,要賣更多課,要好好賺錢...另一邊的我是浪漫感性,告訴我這世界不在這裡,你應該要去他方,去流浪,去成為浪漫一點的作家。
我總有一種感覺,我想把我自己從脊椎的中間撕開,撕成兩半,一半給這個世界,一半給我自己。我常因此睡不著,想死,想毀掉一切,想出家,想放棄我在這個世界的人生,偷渡到某個國家去重新生活。
我有好幾次想要把我的帳號給全部刪了,包括 Substack 的訂閱名單,與過去周加恩告別,換個名字重頭來過。
我真的很想要這樣做,但我總在內心感受到:如果我臣服於這個念頭,那是我的失敗。
在我身體內的爭戰最痛苦的時候,我想起了「與天使摔角」。
在《創世紀》32 章,雅各正要回到故鄉迦南地,與他二十年前欺騙的哥哥重逢。在他渡過雅博河的前一晚,有一個「陌生人」來找他摔角,直到黎明。
這場摔角持續了整夜,那人見贏不了雅各,便在雅各大腿摸了一把,讓雅各腿瘸了,但雅各堅持要那人給他祝福才肯放手。那人便給雅各改了名,改名叫「以色列」,意思是「與神角力者」。
神在此不是以全能者姿態壓制,而是進入人的處境「摔角」。神人之間的關係並非單向的支配,而是摔角:想要祝福嗎?贏了我再說。於是你必須死死抓住神,死命要求祝福,才能贏得。
當「古典理性」的思維與「浪漫感性」的思維直接碰撞,你的內在即處在兩方摔角的狀態裡。
浪漫感性派告訴我,我的帳號是一個失敗品,我必須經歷徹底的毀滅,才有完整的新生。
古典理性派告訴我,我的帳號是一個過程迭代品,我必須堅守在原本的崗位創作。
兩方摔角。
在這個張力之下試著保持冷靜,是非常痛苦的。這是為何你必須在身體上修行——身體是我們與天使摔角的戰場。若沒有打坐與打拳的修行,我不可能承受這場戰鬥,連意識到我正在自我戰鬥的可能都沒有。
但就是在這個張力之下,你會發現一個現實:
你永遠有「餘裕」可以使用。
當你在兩相極端矛盾的狀態之下,你有辦法在兩邊各自探索出「餘裕」(啊搜比),並且試著找到一種「切角」,來同時滿足雙方的價值觀,藉由提升維度解決矛盾。
就像是巴西柔術一樣:許多人都是靠蠻力,但是技巧精湛的人知道巴西柔術是一種解謎遊戲,你永遠可以找到對手關節的破綻,從中固定對手。
你會發現「第三條路」。
雅各與天使摔角,最終的結局竟然是人贏了神——天即將黎明,神懇求雅各放他走(竟然要人的允許!),雅各死死不放,要對方給予祝福才肯放手,於是神給予雅各新的名字,取名叫「以色列」——與神角力者。
第三條路的意義,是當你不斷摔角,在各種餘裕之間討價還價之下,你會重新發現一條路徑,你獲得新的名字,你會成為新的人。這是在張力之下,卡關與摔角帶來的祝福。
在這個張力下,我發現刪帳號不是出路。因為只有我同時處在體制內與體制外,我才能做出更有意義的事情。意即:瘋狂的藝術家多得是,積極的網路創業者多得是,但很少見瘋狂的網路創業者兼藝術家。
成為間諜。「藝術是一門好生意,好生意也必然是一門藝術。」只有在這種極端張力的碰撞之處,在第三條路上,才有真正有趣的事情可以做。
(這句話越是思索,越是感到其中趣味,一個提示:你很難把藝術替換成別的字,回文還仍然成立的。試著把藝術替換成「滷肉飯」、「香蕉」、「AI」等字,你就知道了。為什麼會這樣呢?)
▋ 「第三條路」的特徵
第三條路很難用語言明確定義,且即便我這裡用的是名詞的「第三條路」,但他的概念更接近一種「事件」而非一個你可以抓住的概念,更像是複雜系統的湧現現象。
但我發現,第三條路似乎有四種特徵:
第一個是,「第三條路」必然是出於對人性的關懷。
人性的關懷具有一個目的,意即是「free from concern」,讓人解脫於擔憂。
解脫擔憂的做法不是對他說明擔憂,那只是說教。讓人解脫於擔憂的方法,是引導人「看見」。
好的文學作品,其實都不需要你去說明太多東西。我近期看陳又津《我有結婚病》一書,讓我對女性在華人社會中的處境產生的共感,遠比我在大學時期讀女性主義作品有效太多。她所做就是「show, don’t tell」,把女人的處境單純展現出來,絲毫不帶說教,於是有驚人的打擊力道。
好的喜劇往往直接在舞台上展現情境,而非跟人說道理說教。這是為何很多人不喜歡博恩的喜劇。
「第三條路」的最高目的是「看見」——看見他人,看見這個世界真正存在的處境,讓你成為一個容器,讓世界走進你的身體裡。
這是為何我不認為黃山料是文學家。黃山料的作品中,充滿了太多「應該」,你應該這樣做才是正確的,你應該要這樣,你應該要那樣。
這樣的作品並沒有引導你去看見一個新的世界,我並沒有因為黃山料的作品而更理解「我們作為人的處境」,反而,只有處在焦慮與恐懼的自我狀態下的人會對黃山料的文字產生共鳴——黃山料是傑出的「文案家」(copywriter,擅長用文字激發行動的人),而非文學家。
第二個特徵:「第三條路」必然有質素(Quality)與關照(Caring)。
這陣子我也在思考「文學與我每天傳的 Line 訊息,有什麼不一樣?」,畢竟,我有時候真的很認真寫 Line 訊息,那算文學嗎?
如我前面說的,答案不是在文學絕對主義與相對主義的任何一個極端,而是在兩者之間。我認為「文學性」也是在絕對主義與相對主義之間的碰撞,產生出來的第三條路。包括神性(人與神之間的張力)、幽默(真實與荒謬之間的張力)...這些都是第三條路。
如果用《禪》書中的術語來說,第三條路就是「質素」(Quality)的存在,必須要藉由「關照」(Caring)達成。
「質素」是無法被語言定義的概念,你看兩篇文章,你會覺得有一篇文章比另一篇文章好,但是除此之外你沒辦法再說更多——你可以說無限種理由,但你都無法真正定義出:究竟好在哪裡。
即便我用「質素」這個字,都只是一個近似詞,如禪宗說的「指著月亮的手指」。
但問題是,你一定感受得到「質素」,因為「質素」先於我們的存在。如同你看了 100 個傑出的喜劇演員之後,你就會感受到「啊,有種東西叫做喜劇性/幽默感,但似乎不是所有演員都有——觀眾人數與笑聲與否,似乎跟這種喜劇性無關。」那是什麼?你無法言說。道可道,非常道。
你可以從「質素」的外在展現來簡單感受這件事:「關照」(caring)。
在《禪》書中,作者用「關照」的意思是「對待工作的匠藝精神」,不為外在名利,不為笑聲與掌聲,不為投懷送抱的粉絲,只是單純地想要修煉好他眼前的這門技藝。
工匠用平靜的心上場,面對摩托車的螺帽與引擎,與「維修」成為一體;演員用平靜的心上場,面對數萬人觀眾,與「當下現場」成為一體。
這個「一體性」是質素(quality)的重要展現。
在第三條路上,主體與客體是模糊的,叩門者與開門者是一體的。表演者與觀眾是一體的,是表演者在表演?還是觀眾在表演?是表演者被看見了?還是觀眾被看見了?實際上在演出時,我總感覺隱形的表演者是觀眾而非舞台上的人。
「質素」是清晰可見的。當有一個人引導你,讓你與他成為一體,你絕對會知道。他不會說話,不會張揚,但是當你看見他的表演展現,那會像是對向來車用遠光燈照著你一樣,你幾乎要被他的光芒給弄瞎,像是黑夜中忽現一劈雷,你旋即在幾秒後感受到隆隆雷聲。
第三個特徵:「第三條路」是減法哲學下的產物
可以參照奧卡姆剃刀法則,或者波蘭劇場導演格洛托夫斯基(Jerzy Grotowski)的「貧窮劇場」與 Via Negativa 概念——不用華麗的舞台、燈光、特效,而是單純的演員,演員的身體與聲音,我們藉由移除阻礙,剝除所有非本質的東西,只留下觀眾與演員的相遇,來達到真實的展現。
第三條路是你不斷地移除掉那些不必要的東西,不必要的執著、物品、思考之下,才看見的路。
第四個特徵:「第三條路」是持續的張力。
走上「第三條路」,內在是非常痛苦的,但不是絕望的痛苦,是那種「摔角式的痛苦」,你必須不斷地尋找、討價還價、找到對手破綻、找到施力點...在泥巴裡戰鬥。
雅各式的勝利,並不是完成式的「勝利」——在摔角後他跛腳了,他不知道對方的名字,他甚至沒有完全成為「以色列」這個人,後續的聖經文本仍然交叉使用「雅各」這個名字。
雅各的勝利是進行式的,只要他仍然能承受與神摔角的張力,他就在勝利之下。這是「第三條路」的意義:第三條路是動詞,是當你能承受這個張力,你就在對的路上。張力會成為張滿的弓,把你射到你所想像不到的生命中。
▋ 如何找到「第三條路」
大道至簡,找到第三條路的方式似乎只有一項,那就是「觀察」。觀想、覺察、覺知、內觀....意即「看見」。
既然第三條路的最終目的是「看見世界與他人」,那麼走向這條路的方法也是如此。
所有人最內在的渴望,就是被看見。如果這個世界是以他人組成的,那麼好好看見這個世界與他人,這個世界就會以極豐厚的報賞回應你。
必須要釐清的是:「看見」並不是一套技巧,也不能刻意練習。你可以練習「協助你看見的練習」(意即修行,例如打坐與打拳、舞蹈、音樂等),但是你不能練習「看見」本身。
看見是中性的,無分別心,無造作,無是非,無斷常,無凡無聖地臨在,是「讓你成為我,讓我成為你」的實踐。一但你試圖「掌握看見的技巧」,看見就死了。
技巧是為了一個目的而服務的,把「看見」降格為技巧,你即是把他人與世界降格為「服務於你的目的的手段工具」,你與世界仍然是分割的。這是為何基督教會中強調「我們愛是因為神先愛我們」這句話是非常危險的彎路:這句話非常容易變成「神說要愛人,所以我練習愛人」,於是把「人」降格為你成為優良模範基督徒的工具,你實際上仍然是在利用他人,好滿足你個人的成聖。
因此要真正看見,你的做法必然是一種 Via Negativa,是減法哲學。神必須死,道德也必須死,任何在你生命中,對你偷偷說著「你應該...才對」的語句都必須死,這些都是阻礙。
「加恩,道德死了,那人不就無法無天,燒殺掠擄?」
這是恐懼,回到 Inner Game,這是「自我一」會說的台詞,因為自我一試圖掌控,試圖掌控的背後動力是恐懼的執念。
在網球中,當我們放下「肩膀要放鬆」的執念,單純觀察肩膀,就自然而然會做出正確的動作。
在生活中,放下「我要當好人」的執念,單純觀察「我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我的感受是什麼?在這個當下我是誰?我想要做什麼?我的身體想要做什麼?」,愛自然而然會展現。
你早就有能力看見了,你只需要移除你的阻礙;
你早就有能力傾聽了,你只需要練習平靜;
你早就有能力愛了,你只需要練習放下愛的執念。
大道至簡,但大道極難。
極難是因為:「看見」的能力純粹是身體的,你無法今天說「我要看見」,於是就看見。因為「看見」這個字只是指著月亮的手指,你無法藉由獲得這個字而真的看見,語言必須被屏棄。
那怎麼辦?於是修行。
冥想內觀有用,這不需要多提。
武術訓練有用,泰拳、拳擊、柔術....任何有對戰功能的武術都有用,搏鬥是一種特殊的修行——你與對手成為一體,沒有你與敵人,只有「格鬥」在發生。
拳擊如何成為一種「臨在」的方式?最直接的原因是:你沒有思考的餘裕。拳擊的節奏太快了,你的「自我一」完全沒有發揮的空間,你有時根本無法掌控什麼,只能讓身體自然反應。
拳擊的過程,你面對死亡的恐懼,面對真實挨揍的恐懼,面對必須反應的恐懼。但你不能緊繃,緊繃的身體只會給你帶來過度反應。因此拳擊是一種放下自我的練習。
劇場與舞蹈也是一種修行,希臘神話在劇場中演出,中爪哇的宮廷舞使用舞蹈作為祈禱與神性連結的工具。
詩與音樂也不用說了,吟遊詩人自古是精神性的角色。
茶道、書法、劍道、花道....這些也都可以是。
基本上你聽過中古世紀的禪寺佛寺、不同文化中與宗教儀式可能相關的行動,皆有可能作為修行的一種方式。
當你在這些技巧練習得夠多時,禪會漸漸地進入行住坐臥中,於是無處不是修行,你能「看見」的能力也就越熟練,你越能夠掏空自己,讓他人走進你的生命中。
我知道這很玄,但這是我現在看見的東西,我只能試著把它講出來。
也許使用不同領域的方式,交叉驗證這些修行,會更好「看見」,更感受到「道」也說不定。
每一種工具都是一種「緣」(憑藉),也是一種「障」。但當你看見 50 種蘋果的樣貌,你會更理解「蘋果」的理論概念;當你經歷了 50 種「道」存在的方式,你也會更理解「道」(或者在《禪》書中作者說的「質素」),於是你可以選擇一種修行法門更深入。
▋ 旅行,作為「看見」的練習。
這裡說的旅行,不是單純渡假享受,或單純只走觀光行程的旅行。我說的是一種「學習他人的語言、他人的生活方式、他人如何思考與感受世界」的一種實踐。
旅行是一種「看見」的藝術,看見他人與他方,看見他鄉的喜悅與哀愁。而旅行文學,必然作為一種結案報告,告訴他人你看見了什麼。
「可是加恩,旅遊資訊、Vlog 早就隨手可得了,為什麼還需要你來告訴我你看見了什麼?」
這是非常好的質疑。
我想到的類比是「攝影術」,當攝影術發明之後,畫像也變得隨手可得了,畫出「非常寫實」的畫作的技術變得微不足道。
那麼,畫家從此絕種了嗎?事實上完全沒有,攝影術反而刺激畫家不斷反思:我究竟「看見」了什麼?於是誕生了各種「看見的方法」——結構主義...之類
旅行也是如此。
旅遊資訊普及,才真正解放了我們對於「看見」的貧乏想像,好像所謂巴黎就是鐵塔與咖啡館,義大利就是威尼斯小船與面具節,過去我們都被「觀光資訊」限制了我們看見世界的方法。
而當觀光資訊過度氾濫,這才產生了一個完美的破口:我們終於可以反思,當自己旅行時,我們究竟「看見」了什麼,究竟感受到了什麼?於是不同於以往吃吃喝喝型態的旅行才正要出現。
這種對於「看見」的練習,也是非常珍貴的,你會不斷打破你自己的框架,才發現原來味增可以拿來做成拿鐵(Austin 咖啡廳),原來天婦羅可以炸 Jalapeno 墨西哥辣椒(San Antonio 日本料理店),原來工作到下午是可以去睡兩個小時的午覺的(西班牙),原來馬桶上面直接裝一個水龍頭也是可以沖水的(義大利)。
他人的世界是一面哈哈鏡,照了之下才看見自己的世界其實挺可笑、荒謬的,是可以解構的。
▋ 這個時代最寶貴的技能是什麼?
老實說,我對 AI 的興趣真的非常快速地消融了。
回台灣跟一位好朋友聊天,她以前非常積極投入 Vibe Coding,但現在她的感受是:「我很確定這件事會成立了,AI 協作的 Coding 是下一個 huge thing,但既然如此我就沒興趣了——反正一定都會成,成就不需在我。」
我對 AI 寫作也是大概這樣的感受,反正我很確定這件事會成立(或者已經成立了),那我對這件事的興趣就消失了。
我這個月,我大概也是在做一種探索:這世界上最寶貴的技能,是什麼呢?能帶來最大報酬的是什麼?
技能帶來價值,因為技能滿足了世界上某種缺乏。
那麼,世界上最普遍的缺乏是什麼?
「被看見」。
每一個人,都渴望被看見。
我們都渴望心中模糊的感受被痛快地說出來(喜劇演員的功能),生命處境的無奈被好好言說(文學家的功能),生活的不舒適與不方便痛點被舒服地解決(創業家的功能),我心中最軟弱的一塊可以被接納(愛人的功能)。
所有人最內在的渴望,就是被看見。
被愛。
我才意識到,這世界最缺乏的技能,最寶貴的技能,就是「看見」與「傾聽」。
我們根本不需要更多「會說話的人」了,這世界才不缺乏另一個說教男。
我們極度缺乏「擅長傾聽的人」。
我活了這一輩子,真正擅長「傾聽」的人,我似乎只見過少數一兩位。(以傾聽為專業維生的諮商師除外)
大多數的人所謂「社交生活」,即是輪流說話,輪流強迫他人看見自己,並且希望這個過程還勉強可以忍受。這是多可怕的地獄!無怪乎我從大學就討厭跟人社交,不是因為我討厭人,是因為我討厭這種無明的集體取暖——我們都在一起,但沒有一個人真正看見他人。
大多數人,只看見自己內心的慾望,投射在他人身上的樣子。說教男在他人身上看見「展現我有多聰明」的大好機會;PUA 男在女人身上看見「展現我有多性感」的大好機會。
這世界渴望被看見。
從這裡,我也在重新思考「Manner」的意義。對我來說,一個普通人與貴族之間的差別不是在錢,而是貴族知道什麼叫做 Manner,也擅長 Manner。
manner 一般都翻譯成「禮節」,但這個字在今天已經越來越貧乏而疲弱。
我認為 Manner 是一種單純的利他主義,一種「我希望他人在我身邊可以盡量舒服自在」,從這個出發點為他人著想的社交技巧。
「進行一個好對話」尤其是 Manner 的重要環節,知道怎樣與他人對話,是讓別人在你身邊感到舒服自在的方法。
「主動傾聽」就是對話的一切了。
「傾聽」幾乎是「愛」的同義詞。
如果這世界上有一種可以練習的技巧,是最接近開悟的,那就是「傾聽」:聽人的對話,聽人的氣,聽觀眾的氣,聽人所沒有說的語言。讓對方走進你的身體裡,把自我掏空成為容器。
如果你願意練習發自內心地看見這世界,傾聽這個世界所要說的話,我的個人體驗是,這世界會以驚人的美好回報你。
▋ 結論
這一個月,我的起點是「放下所以試圖掌控的意念,單純讓世界走進我身體裡」。
我發現單純只是「讓事情發生,不拒絕,叩門的就給他開門」,這世界以驚人的共時性展現在我面前——我所有的問題都被回答了一輪,我的自我爭戰沒有結束,但我意識到「與天使摔角」的意義,並且欣然地接受這種征戰,我意識到身處在「張力」之中,即便痛苦如撕裂自己,帶來的會是人格的轉化。
這篇文/podcast,即是我的這個月的結案報告,對我來說是一種旅行文學——我在精神世界探索一輪之後,回頭來告訴你我看見了什麼。
《馬太福音》中有一段知名的章節:「尋找的就得見,祈求的就得著,叩門的就給你開門。」
這段過去都用來解釋「如果你缺乏什麼就在禱告中求,天父會給你回應。」
但叩門的是誰呢?開門的是誰呢?也許反過來說也成立:當世界在叩你的門時,你願意給他開門嗎?
我們過去都受限在偏見、恐懼、質疑、執念中,不斷質問世界來者何人,有何貴幹,但實際上這都造成了太多的苦難。也許下一次當苦難出現對你叩門,你就開門,單純地讓苦難進來成為你自己——成為一體。抗拒痛苦,往往製造了更深的痛苦。
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得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這句話沒有主體客體之分,也許世界總在尋找你,祈求與你對話,對你叩門,而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放下掌控——Don’t try,給世界開門,讓世界走進你的身體裡,領受這世界將給你帶來的豐厚恩典。
PS:這篇的語言特別紊亂,可能很難理解,真是抱歉。
一方面是我想描述的東西真的不容易捕捉,另一方面是「道」存在於語言之外,如果試圖用語言捕捉,你就注定什麼都捕捉不到了。道可道,非常道,這是真的,我只能用很鬆散的語言,試著捕風捉影。
所以現在我對那種所謂的「上師」,或者任何自稱為「開悟」的人,都一律認定是放屁。開悟的人不會出來宣稱自己開悟了,一但宣稱了,開悟就變成一套技巧,世界又再次成為了服務於你的自我的工具,你又處在與世界分割的關係裡,這是反開悟的。
禪宗說:「如果你在路上看見佛祖,殺了他」,因為佛不需要自稱,佛性在每個人身上。佛在電路板裡,佛在機車引擎汽缸裡,佛在每一行 code 裡;佛也在你每一天相遇的人,你最親密的夥伴,你的敵人裡。
(有時他們是同一人。)
新年快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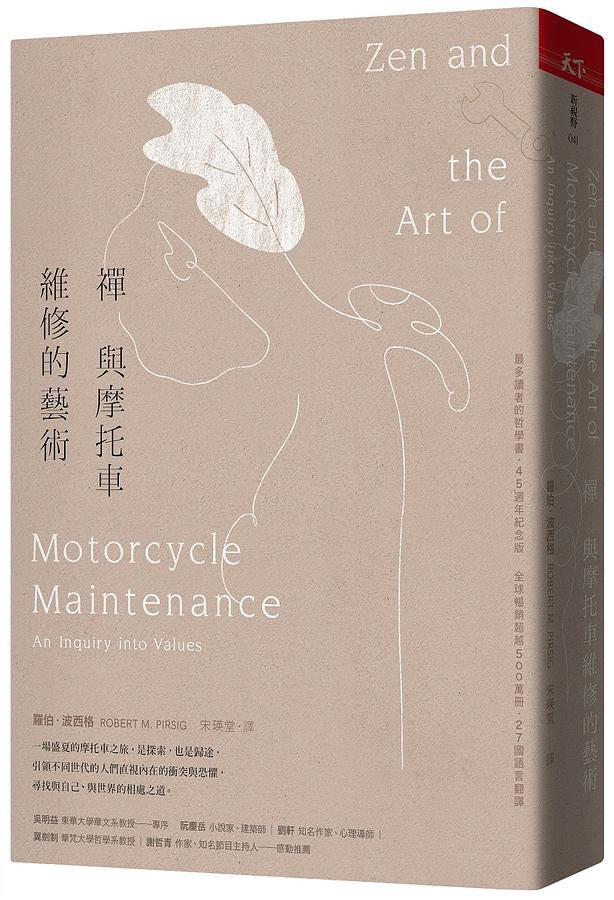
我是在電子報看到這篇文章的,我很喜歡你的這篇文章,就像你結語說的,整篇文章很散亂不好閱讀,但不知為何我就是覺得要讀下去,甚至回頭去把我一度覺得混亂匆匆帶過的片段再讀一次。中間有好幾句話,我都覺得是在跟我對話;有些則像是在回答我之前與自我對話時的疑問;有些話則讓我一讀就很被觸動內心。
我也在尋找自己的路上,我也有過冥想過程或閱讀阿卡西記錄過程,接收到很豐富很觸動的資訊與感受,但卻無法落筆寫下,當時我以為是自己文筆不好,但今天知道了原來並非如此。
我深信今天與你這篇文章的遇見,是宇宙在最適當的時間點送予我,這篇文章回應我很久之前的提問,也為我近期的疑惑解答,很感謝你寫下這篇文章
好喜歡你的文字,尤其「與天使摔角」中內心的拉扯,我有所共鳴。
雖然有些不完全理解的段落,但我也想努力成為那樣,個人想法中富含滿滿價值的作家。(我讀的書還遠遠不夠)或許不會成為作家,更可能成為創業家,若能成為一位藝術家,那會是很高的讚揚。
已經看過不少你的文章,這是第一次留言,想謝謝你像這樣寫下發人深省又觸動人心的文字,給我看待事情的新觀點、再度感受書寫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