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的藝術
如何在懊悔、虛無、執著中找到力量。
嗨,好久不見,兩個月了。
跟你報告我消失的原因:去年做《電馭寫作》課程真的是衝過頭了, 11 月底,我 burn out 了。
burn out 來得無聲無息。即便我早就讀過 burn out 相關的書,非常小心「監控」自己的倦怠程度,都沒有用。
在那當下,我總是會想著「我有休息了,我應該可以再工作。」沒有,可能任何休息都不夠。burn out 似乎有一個不可逆的骨牌效應,一旦越過了門檻,就會啟動死亡螺旋:我只能停止寫作、停止經營社群、停止回覆訊息。
這兩個月,我走了一趟自我懷疑與崩潰的精神谷底。
這場 burn out 也留下詭異的心理創傷:那些我努力做出來的成績,恰恰就是我痛苦的來源——因為不斷強迫自己衝刺的結果。
我開始厭倦過去的所有成就。這兩個月中,我曾經很認真地想把臉書跟 Substack 賬號給刪了,把所有東西通通燒毀,徹底換個工作,去當個汽車維修技師之類的——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還好我把自己拉住了。足足花了兩個月,我才慢慢爬出這個谷底,回到正常狀態。
不過,就在這個谷底中,我似乎撿到了一個很重要的寶藏,變成讓我重新爬起來的力量。這個寶藏的名字,叫做「失敗的藝術」。
這個失敗,不是一般人平常說的失敗,
不是「失敗為成功之母,要勇敢面對失敗」之類的雞湯學;
不是「失敗就是快速迭代,從 MVP 開始」的矽谷成功學;
也不是「沒有得到升遷的日子,被欺負,被霸凌,被排擠,被公審,被忽略,被遺忘...」這些外在事件的失敗。
我說的是「內在的失敗」。是一股細微的聲音,每日每夜,不停嚙咬著你的心臟,輕輕在你腦中說著:
不管你是誰,不管你多努力多成功,這個失敗永遠陰魂不散,永遠在你背後低語,更像是一種「生命能量」的存在。
紫微斗數中,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由十四個主星組成的,每個「星曜」各自散發能量,影響你的人生。
我說的「失敗」,很像紫微斗數的「星曜」——所有人的生命中,都有這股「失敗」的能量存在。不是因為你有問題,只是因為「失敗」本來就是自我的一部分。
主流世界無法接受失敗。成功學講師會說:「要征服自己的慾望,克服自己的惰性,要有紀律,自律的女人有多可怕...(永遠忘不了 NanaQ 這個口號)。」這世界要求你打敗「失敗」這個內在能量。
這很勵志沒有錯,但問題是:這樣的人生注定是悲慘的。
「失敗」既然是自我的一部分,試圖打敗失敗,就是與自我為敵——我們都知道自殘不好,為何要在精神世界裡自殘,要跟自己過不去呢?
既然「失敗」是自我的一部分,那我們就值得好好認識「祂」。1
在這兩個月中,我開始練習與失敗相處,像是邀請朋友來家裡一樣,我試著觀察「失敗」,跟祂喝茶、喝酒聊天。
然後我才發現,「失敗」其實個性還不錯。
失敗的三種身份
我從小就害怕失敗。
我還記得小時候,我最愛的遊戲是《世紀帝國》。但我沒有成為那種戰略天才的電玩兒童,因為開始玩不到一個月,我就發現可以輸入秘技獲得無限資源(aegis,還有傳說中的眼鏡蛇車...)。因為秘技,我永遠不會失敗,但我也從來沒學會什麼叫「策略遊戲」。
因為害怕失敗,我很少好好看著「失敗」的臉孔。
直到這兩個月刻意觀察,我看見:失敗表面上看似一團混亂,其實內在有模式可循。
你有看過那種「視覺魔術繪本」(Magic Eye books)嗎?你的眼睛要瞇出個特定的力道,稍微有點失焦,換個視角,然後你會看見 3D 的影像浮出畫面。
「失敗」有點像是這樣。
表面上看起來,失敗就是失敗,沒有意義,一片混亂,一堆雜訊。但是當你用對視角,眼睛瞇成一個剛好的力道看祂時,你會發現:「失敗」的能量是來幫助你的。當你越是擁抱(甚至熱愛)失敗,失敗就越能轉化成力量來源。
怎樣轉化呢?
也許,我們可以先從失敗的「多重身份」來認識祂。
紫微斗數的星曜,很像希臘神話的眾神:每個星曜都有自己的個性、強項與弱點。太陽星主掌事業與光明,對應阿波羅(Apollo);貪狼星主掌情慾、享受與才華,對應阿芙羅黛蒂(Aphrodite)。
「失敗」如果是一種星曜,那祂就是一個狡猾的惡作劇角色,身懷多張「面具」,隨時換一張來跟我們周旋。
我所能辨認出來的「失敗」有三張面具,每張都在跟你說著只屬於祂的台詞;這些台詞看似悲觀,卻是可以被轉化的力量泉源。
這三張面具,就是「懊悔、虛無與執著」。
失敗的第一張面具:懊悔。
懊悔的台詞:「無論你選擇什麼,你永遠都會後悔」。
在這兩個月谷底中,我發現:
我最害怕的不是做了一件事然後失敗;
我最害怕的,是投入了好幾年人生做一件事,甚至成功了,但我卻後悔了:搞了半天才發現,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成就。
我人生第一次面對「懊悔」,是高中。
整個高中對我的意義,就是考上台大。我完全不玩樂,把自己封閉起來,不交朋友,不玩社團(我加入生物研究社...),只專心讀書。
三年過去,放榜日到來,我坐在教務處的電腦前點開榜單:
台大生化科技系:周加恩 錄取
台大植物病理學系:周加恩 錄取
台大生命科學系:周加恩 錄取
我申請台大三個科系,全上了。
我似乎應該開心的,對嗎?我卻什麼情緒也感覺不到,沒有興奮,也沒有難過,沒有懊悔,甚至沒有疑惑——什麼都沒有。
電腦螢幕散發著令人發寒的空白。坐在教務處的搖晃辦公椅上,我的身體不斷下沉,掉進一個無盡的黑洞裡。我背後響起了一個聲音:
「就這樣嗎?」
「我犧牲了三年的青春,就為了這三行字嗎?」
「那接下來呢?我又要犧牲什麼?追求什麼?」
補習班老師幫我做了紅布條,上面寫著「台大三冠王」,刺眼地掛在教室的鐵窗外。我還是照樣去補習班,但我總試著繞開那個紅布條。
一直到了畢業之後,我才跟班上的同學熟起來,才知道這三年有哪些班對,誰玩熱音社跟別校女生交往,誰討厭誰誰誰的抓馬。
我寧願我根本沒有選擇「台大」這個目標,至少好好交朋友,享受高中生活,好好考個一般的大學。
這是失敗的第一張面具,「懊悔」。
我們總試著努力找出那個「不會後悔」的選擇,告訴自己:「選你所愛,愛你所選;選了,就不要後悔。」
這些是經典的雞湯,聽起來都很好,但只有一個小問題:人活著要不後悔,不可能——
結婚吧,你會後悔的;不結婚,你也會後悔。無論你結婚還是不結婚,你都會後悔。
嘲笑世界的愚蠢,你會後悔;為它哭泣,你也會後悔。無論你嘲笑世界的愚蠢還是為它哭泣,你都會後悔。
相信一個女人,你會後悔;不相信她,你也會後悔⋯⋯
上吊吧,你會後悔;不上吊,你也會後悔。無論你上吊還是不上吊,你都會後悔。
這,先生們,就是所有哲學的本質。」
—— 齊克果.《非此即彼》
你的每一種選擇,都會關閉其他無限種選擇,伴隨無限的犧牲與代價。你永遠都會後悔,只是後悔的程度多寡。
所有選擇都是錯的,你只能選擇一個自己比較願意承擔的錯誤。
「天啊加恩,你這太悲觀了吧!」
確實,這是極度悲觀的。但我結論並不是「反正都會後悔,幹嘛要追求?乾脆放棄吧!」的悲觀虛無。
相對的,我想提倡一種「激進的悲觀主義」:
既然我追求的每一種結果,我得到的時候一定都會後悔;
那麼,有哪一件事是「即便結果會後悔,我也想要全力投入?」
既然「結果」一定會後悔,那就沒有所謂的「現在忍一忍,等到上大學/升遷/加薪/換工作...之後就好了」的事情。
我們只能轉向「過程」:當下的工作本身就必須是快樂,是意義感的來源,與結果無關。
於是你可以對抗風險:如果你享受過程的每一刻,那當你到達「結果」時,開心還是後悔都不重要了。你不受懊悔影響。
希臘詩人 Cavafy 的詩《Ithaka》,很漂亮地闡述了這個概念:
讓伊薩卡永遠存在你心中,
抵達那裡,是你的命中注定。
但是,可別匆忙趕路了,
最好,你的旅途要花上個好幾年,
當你到達時,兩鬢已然蒼白,
一路上的旅程,已經收穫豐盛,
你不需期待伊薩卡給你什麼。
伊薩卡給了你美好的旅程,
沒有她,你絕不會出發,
而現在,她也沒有什麼好給你了。
如果伊薩卡不如你預期,你並不會失望,
路程已經使你智慧,讓你閱歷豐富,
於是你會理解,伊薩卡們的意義何在。
伊薩卡(Ithaka)是英雄奧德修斯(Odysseus)的故鄉,在特洛伊戰爭結束後,他花了整整十年才回到家——這十年間,他經歷了獨眼巨人、女妖賽倫的歌聲、卡律布索女神的島嶼、吃了忘憂果的同伴、在冥界與亡靈對話...總之,無數的冒險與考驗。
Cavafy 這首詩《Ithaka》則是把「回家」的意象,轉化成「求索」:願你尋找伊薩卡的旅程,漫長、蜿蜒又曲折。如此一來,當你真的抵達了,即便伊薩卡讓你失望,你也不會太失落,因為旅途已經帶給你太多風景。
路途,就是旅程的寶藏。
在經典靈性探索小說《Snow Leopard》中,作者 Peter Matthiessen 也在尋找他的伊薩卡:他出發到尼泊爾山區尋找「雪豹」——傳說中的優雅掠食者。
艱苦跋涉的兩個月過去了,他看見了雪豹的腳印,看見了竄逃的野綿羊(顯示雪豹可能在附近),看見了被困在山上八年,內心卻充滿喜樂的喇嘛,看見了稀有的喜馬拉雅藍羊,——但就是沒有傳說中的雪豹。
在小說中,他自問自答:
“Have you seen the snow leopard? No! Isn’t that wonderful!”
「你有看見雪豹嗎?沒有!這不是很棒嗎?」
他的旅程結果是失敗的;但從過程看,這是最豐碩的旅程。他一路上已經看見太多寶藏了,也許讓雪豹繼續神秘是最好的結果。
這是「懊悔」帶給我們的禮物。
當你瞇著眼睛,用著剛剛好的失焦去看「懊悔」,會浮現出什麼呢?是無悔?是滿足?
對我而言,浮現的是「真實」。
因為完全接受了「任何努力必然伴隨後悔,尤其是為了滿足他人而做的努力」,這是專屬於失敗者的解放——我們可以選擇最貼近於你自己真實的行動,把所有「為了未來,忍一忍現在」的選項都刪除。
用最真實的聲音說話,做出最真實的作品,選擇最真實的行動。
失敗的第二張面具:虛無。
虛無的台詞:「虛空的虛空,一切都是虛空。」
虛無主義,也許是每個人成長路上,都必經的一條路。
退伍之後,我和家裡鬧了一場革命,放棄了去西班牙唸牙醫的機會,選擇留在台灣做單口喜劇。
當時我很喜歡讀卡繆的《薛西佛斯的神話》,只覺得人生充滿荒謬,所有努力都沒有意義。我人生寫出來的第一個笑話,也帶有一點虛無主義的色彩:
人生就是不斷的上上下下。
小時候上學下課;
長大了上班下班;
等你死了,給你上香下葬。
好笑吧,哈,哈,哈...
虛無。
我們期望世界是有意義的,期望努力會有結果,期望可以理解這個宇宙,期望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但現實是:宇宙根本不屌你。好人受苦,惡人得意,戰爭落在無辜的人身上。我們尋找伊薩卡的努力,無論成功或失敗,開心或後悔,最後只有一個結局:死亡。
「銀鏈折斷,金罐破裂,瓶子在泉旁損壞,水輪在井口破爛,
塵土仍歸於地,靈仍歸於賜靈的神。
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傳道書 12:6-8》
當你質問宇宙「為何如此?」,宇宙只是沈默。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宇宙不需要回答人類,人類只是風中一粒沙塵,一根稻草。
人類對意義的渴望,撞上了宇宙的沈默,兩者之間的斷裂,就是卡繆所說的「荒謬」。
卡繆用「薛西佛斯的神話」來比喻這種荒謬:薛西佛斯,凡人裡面最精明的,背叛了宙斯,綁了死神,耍了冥王,最後被眾神懲罰每天推巨石上山頂,讓巨石自由滾落山底,不斷重來——直到永恆。
無意義的勞動,就是他的懲罰。
卡繆說:我們都是薛西佛斯,每天推著屬於自己的石頭,看著石頭滾落山腳,然後重來——直到死亡。巨石滾落的聲響與沙塵,對我們發出了嚴格的質問:
「如果每天的努力都是虛無,那為何還要努力呢?」
如果清醒地面對這虛無的荒謬,你會發現我們落入了「毫無選擇」的處境:你根本沒有選擇進入荒謬(我們可沒簽署「被出生同意書」),你也不可能逃離這個荒謬的處境。
我們都是薛西佛斯,被眾神丟入荒謬之中。
那麼,卡繆怎樣處理「荒謬」的問題呢?
在《薛西佛斯的神話》中,他首先排除掉三個路徑。
第一個是「自殺」——他說:人生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你為何不自殺」。既然一切無意義,那為何不早早結束?但卡繆否定自殺。荒謬是人與世界之間的張力,當人消失,荒謬就消失,你並沒有真的解決荒謬,你只是破不了關,就把遊戲主機的電源線給拔了。
第二個路徑是「神」——為何不像齊克果那樣訴諸信仰,讓上帝給你生命的超越意義,拯救你脫離荒謬呢?卡繆認為這是用虛構的答案來回答問題,是放棄思考的「哲學自殺」,只是對荒謬的逃避。
第三個路徑是「虛無主義」——既然一切的都是荒謬,那道德標準也是荒謬的,想殺人殺人吧!想放火放火吧!卡繆也否定這點。荒謬是來自兩個極端的碰撞:「人渴望意義+宇宙沈默」,如果從荒謬中推論出「想幹嘛幹嘛的虛無主義」,那就是否定了渴望著意義的人性。恰恰因為這個人性,卡繆說:「荒謬不解放,而是束縛。它不授權所有行動。」
「加恩,我不能就當作沒有虛無這一回事,繼續過我的日子嗎?」
當然,我們可以用資本主義為你準備的各種小東西來轉移注意力(奶頭樂、社群媒體、酒精、電動...),但這就跟自殺或信仰一樣,沒有真正解決荒謬,只是逃避。
卡繆說:唯一的出路,是「反抗」。
“Je me révolte, donc nous sommes“
「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回到一開始的公式:「荒謬=人渴望意義+宇宙沈默」。
反抗,就是明明知道宇宙永遠會沈默,荒謬永遠不會解決,但仍然選擇人性,選擇渴望意義——甚至更用力地去追求意義。
眾神對薛西佛斯的懲罰,並不是單純「推石頭」的體力勞動。石頭一次又一次地滾下山腳,薛西佛斯清楚知道石頭永遠會滾下來,他永遠無法脫離這個「無意義」的懲罰。
眾神真正想看到的,是薛西佛斯被「絕望」壓垮。
但是,叛逆的薛西佛斯,會這麼簡單地甘願讓眾神得逞嗎?肯定不會。
眾神可以強迫薛西佛斯推石頭。
眾神不能強迫薛西佛斯絕望。
薛西佛斯的課題非常清楚:「在這個看似再也沒有希望,永遠沒有意義的反覆勞動中,我如何創造,並且追求屬於我的意義?」
卡繆在書中,給出一個關鍵句子:
“There is no fate that cannot be surmounted by scorn.”
「沒有任何命運是不能被蔑視所超越的。」
原本,推石頭的命運是眾神強加給薛西佛斯的,他是被動的接受者。
但是,叛逆的薛西佛斯拒絕臣服命運,清醒地面對虛無,說:
「去你媽的眾神。你們可以決定我的處境,但你們不能決定我對處境的態度。態度是我的領域——人的領域。」
「既然我永遠逃脫不了這個處境,既然眾神想看我被壓垮,那我就主動擁抱這個命運。」
薛西佛斯把命運從眾神手裡搶了過來,變成了他自己的命運。
石頭不再是懲罰的工具,而是「他的石頭」。
卡繆繼續說:
“All Sisyphus’ silent joy is contained therein. His fate belongs to him. His rock is a thing.”
「薛西佛斯所有沈默的喜悅都包含在這裡。他的命運屬於他。他的石頭只是一個東西。」
甚至,因為他的積極選擇,他可以在自己被懲罰的處境中,看見只屬於這個處境的美好:
“This universe henceforth without a master seems to him neither sterile nor futile. Each atom of that stone, each mineral flake of that night filled mountain, in itself forms a world.”
「這個從此沒有主人的宇宙,在他看來既不貧瘠也不徒勞。那塊石頭的每一個原子,那座充滿夜色的山中,每一片礦石碎片,都是一個世界。」
“For the rest, he knows himself to be the master of his days.”
「至於未來,他知道自己是他日子的主人。」
薛西佛斯的故事是一場內在的精神戰爭:眾神希望他絕望,但他竟然還能在極度無意義的反覆勞動中,找到了屬於他的意義,成為他日子的主人。
眾神再一次被薛西佛斯打敗了。
因此,卡繆說出他的名言:
“One must imagine Sisyphus happy.”
「我們應當想像薛西佛斯是快樂的。」
讓我們再次瞇起眼睛吧!靜靜地看著虛無,讓眼睛有點失焦,有點用力又放鬆...你看見了什麼呢?我看見,在虛無的黑洞深處中,有一個隱隱幽微的光芒,輕輕地說著一句話:
「為何不跳舞呢?」
是的,跳舞。
我看見的是:虛無的反面不是存在,而是跳舞。
現代社會,總想要我們把一切都當成工具手段。
大學是工具,目的是為了得到最後那一張學歷證書;
學歷證書,是為了找到好工作;
好工作,是為了賺錢;
賺錢,是為了快樂。女人與男人是工具,目的是愛情;
愛情,是為了婚姻與看似美滿的生活;
婚姻與看似美滿的生活,是為了快樂。朋友是工具,目的是不要孤單;
不要孤單,是為了證明我有價值。
證明我有價值,是為了快樂。
為了「快樂」這個最終目的,我們卻把身邊的友誼、愛情、激情、知識...都降格為工具——我們試圖剝削這個世界的一切美好,就為了讓自己快樂,這不是很蠢的一件事嗎?
虛無,以及祂內在的幽微光芒,對這一切說:
「這是幹嘛呢?
繞了一大圈呀,為何不跳舞呢?
繞了一大圈呀,為何不唱歌呢?
繞了一大圈呀,卻什麼也得不到;
為什麼不牽著愛人的手,一起唱歌跳舞呢?」
跳舞為了什麼呢?跳舞可以積累出什麼呢?跳舞有什麼生產力呢?什麼也沒有。
但是,只要有人類文明的地方,就有跳舞。
跳舞帶來快樂,跳舞讓你的身體充滿彈性(不需要花錢按摩!),跳舞讓人們親近彼此。
因為跳舞,我們反抗虛無。
這個跳舞可以是真的跳舞,也可以是把日常重複勞動變成舞蹈:洗碗是跳舞,填表格是跳舞,寫 code、跟客戶溝通都是跳舞。
既然是跳舞,我們就可以思考:怎樣讓洗碗的動線最短?怎樣把韻律結合動作?怎樣發一封訊息就照顧到客戶的所有顧慮?怎樣讓填表格變成好玩的工程問題?
於是日常的勞動,就產生了美感與意義。
薛西佛斯在巨石的每一個原子、每一片礦砂中看見意義,我們應當想像薛西佛斯是快樂的,因為他跳著屬於他的推巨石之舞。
寫作是我的巨石。我寫的所有東西,終將飄散遺忘。虛空的虛空,一切都是虛空。
寫作也是我的舞蹈。我知道這一切都沒有意義,於是每一次思考字句、反覆改寫文章,本身就是快樂與美感的來源。
我們怎能說「虛無」是壞消息呢?
沒有命運是不能被蔑視超越的,在反抗的舞蹈中,我們都是日子的主人。
失敗的第三張面具:執著。
執著的台詞:「為了達成目標,我一定要放棄某些東西。」
人的痛苦,往往不是來自於痛苦本身,而是來自於對痛苦的逃避。
莊子《外篇》有一段經典故事,叫《華封三祝》: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
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
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
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2
來個白話翻譯:
堯聖巡查華區,封人(當地基層小官)對堯聖說:「哎,是聖人!我給聖人敬酒。」
「祝您壽比南山!」
「別了吧。」堯聖說。
「祝您家財萬貫!」
「別了吧。」堯聖說。
「祝您子孫滿堂!」
「別了吧。」堯聖說。封人問:「長壽、錢財、子孫都是大家想要的東西,您卻不要,這是為何呢?」
堯聖說:「生許多子孫就怕他們出事,有許多錢財就有管理麻煩,活得太久恐怕被人羞辱。這三件事都跟修養德性沒有關聯,所以別了。」
封人說:「我以為您是聖人,原來不過是個君子而已。」
「每個人生來都有天命,您生許多子孫就讓他們去找到自己生命的出路,那有什麼好怕的呢?您擁有許多錢財,都分給窮人,那還有什麼好管理的呢?所謂聖人,活得像鷓鴣一樣居無定所,吃得像幼鳥一樣母鳥給他什麼就吃什麼,像是鳥一樣活著,不需彰顯自己的德性;當世界繁榮時,就跟萬物一起共榮;世界混沌時,就回家修身養性,閒散度日;活了千年對世界厭倦了,就化作仙人,乘著白雲到天界去。您說的三種麻煩事,都煩不了聖人,那活得長壽又怎樣會被羞辱呢?」
說完封人就走了。
堯聖追上去:「等等,讓我再問你...」
封人:「閃啦。」
在堯聖的世界觀中,擁有是一種承擔,家庭是一種承擔,活著也是一種承擔。承擔越多,距離聖人就越遠,所以堯聖拒絕長壽、子孫、財產——把任何跟聖人無關的東西都斷捨離了,連別人的祝賀都要無禮地拒絕。
莊子則用封人的嘴點出堯聖只是「表面的極簡主義」,實際上仍然執著於「聖人就應該怎樣」,所以逃避那些和執著衝突的事情——長壽、財富、兒子。
真正的聖人是超越執著的,不追求「擁有」,也不追求「不擁有」,活得跟鳥一樣沒有牽掛——鳥形而無彰。既然無所牽掛,世間就沒有什麼東西是「承擔」了,無所謂重,無所謂輕:
有了財富,就分給眾人吧;
有了兒子,就讓他們自己找事做吧;
有了長壽,就活得像鳥吧。於是「三患莫至,身常無殃」。
這種超越當然是很好,問題是:怎樣才能超越執著?連堯聖都超越不了,我們又怎麼辦呢?
在這兩個月的谷底中,我意外發現:超越執著的方法,似乎就是清醒地,靜靜地觀察執著。
只是觀察。
我多次考慮過把臉書與 Substack 帳號刪了。為什麼想這樣做呢?除了 burn out 的創傷以外,另一部分是因為:
一直以來,我想要當的是作家,不是 AI 講師。
我過去的文章裡的「周加恩」太追求效率了,太正向了,太行銷了,太...媚俗了。
12 月回台灣參加大學同學的婚禮,看見自己的介紹是「AI 寫作大師」。朋友是滿心的好意,但我看著那個稱謂,好像又再次看到當年「台大三冠王」的紅布條,眼睛又刺痛了。
過了幾天,我的身體浮現出某種執著,竟然開始對我說話了。
「這不是你。」
「你走的路已經錯得太離譜了,我們必須把一切燒掉——去當個雲水僧,單純浪跡天涯;或者去泰國寺廟出家,單純當個和尚吧。
當和尚的作家,流浪世界各地的作家,不是有趣許多嗎?」
從這天起,整整兩個月,執著每天來拜訪我。只要我醒著,「燒毀一切」的執著隨時都會出現:在我洗碗的時候,睡醒的時候,做夢的時候...每日每夜,我反覆與這個執著激烈辯論。
甚至,這執著竟然逐漸壯大,漸漸有了形體!我感覺到執著在我的積極對抗中獲得了能量,在我身體裡佔了一方地盤...
「它」,竟然變成了「祂」。
我開始對這個執著好奇。
為何祂不斷回來呢?祂究竟想說些什麼呢?
我決定不再對抗,只是靜靜觀察祂。
有時祂展示歐洲流浪的浪漫;
有時祂引用禪宗,「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有時祂咆哮「還在這裡做什麼,你傻啊?」;
有時祂什麼都不說,只是啃咬我的喉嚨與脊椎。
不舒服,當然不舒服,讓人想死的不舒服。
我恨不得脊椎上有一條拉鍊,讓我把身體撕開變成兩半,一半的我去流浪,另一半留下來建造我的事業。
但我無法。
執著,變成了我的薛西佛斯巨石:眾神把執著丟到我面前,我知道祂是殺不死的(是自我的一部分),我只能盡全力觀察祂——讓我清醒地面對荒謬。
隨著我不斷觀察執著,我越來越佩服了:祂竟然真的每次都帶不同的東西來說服我!我不得不欣賞祂的創意。
我開始稍微主動歡迎祂,把祂當成朋友對待。
有天晚上我再次失眠,凌晨三點多獨坐在廚房,看著寂寥的客廳發呆。
執著又來了。
這次祂沒有帶新東西來,只是重新把老招重演一次:再次啃咬喉嚨,再次邏輯說服,再次強硬態度,再次歐洲流浪。
我靜靜看完這一切,只回應祂:「嗯哼,我聽見了。還有嗎?」
祂沈默了一陣子。我幾乎聽見祂嘆了一口氣,兩手攤開在胸前:
「我只是想要你行動,做點什麼。」
「我不能接受你停滯在這裡,我不能接受你什麼都不做。你會死,你的靈魂會死,你的身體會死。」
「我不會讓你死。」
「什麼都好,行動吧。」祂這樣說。
在這一刻,我好像,與祂稍微和解了。
停筆了兩個月,我終於開始寫作。
敲打鍵盤的時候,執著也在一旁默默看著,在我寫不下去的時候推我一把:「給我行動!」;
我懶得出門運動時,執著也在旁邊刺我一下:「什麼都好,行動吧!」於是我出門。
執著仍然每天來找我,但我們的關係已經漸漸不一樣了——我們仍然發動戰爭,但過程更像是一種以武會友的對練(sparring) ,而不是你死我活的廝殺。每一次與執著交手,我都更強大了一點點。
執著,醞釀著我們最深刻的在乎。
執著表面上想來控制你,但如果我們最後一次瞇起眼睛,仔細盯著「執著」看,聽聽祂究竟想要說什麼,你會發現:執著的反面,是生命中最深刻的「力量」。
斯多葛哲學有句名言:「Obstacle is the way」。
直接面對障礙,就是唯一的出路。
直接面對「逃避一切」的執著,祂就從人生的阻礙,變成行動的力量。
卡繆說的對:那本來折磨我的清醒,最後確實為勝利加冕了。
怎樣練習失敗的藝術?
「失敗的藝術」這個詞,最接近的書是《The Queer Art of Failure》,但書中內容太學術了,我看不下去。
這篇文章,只是被這個書名啟發,用書中的切角來反思我這兩個月精神低谷中獲得的東西,名之「失敗的藝術」。
怎樣練習失敗的藝術?
▋ 1. 觀察
只是觀察著懊悔,久而久之,就看見了「既然必然懊悔,那就做最真實的行動」;
只是觀察著虛無,久而久之,就獲得了「反抗的舞蹈是唯一出路」;
只是觀察著逃避,久而久之,才知道逃避的另一面即是行動,是打破當下僵局的勇氣。
這個觀察是辛苦的,會是很多個難熬的夜晚——崩潰、淚水、蜷曲著質問宇宙。但最後的收穫是值得的。
▋ 2. 身體
因為過程很辛苦,針對身體的修煉就非常重要。
我的經驗:只要有在打泰拳,我就能更清醒地觀察失敗;但是當我偷懶不運動,我就幾乎無法承受失敗的攻勢,很快就會用酒精麻醉自己。
單純只是跳舞也很有用。什麼舞都可以,我不會 breaking,但我會跟著音樂亂扭,反正我在房間沒有人看到。我才不管跳得多好看,重點是爽。
或者,任何針對身體的練習,冥想、武術、舞蹈、瑜珈、太極....也都是修煉「失敗的藝術」的底子。重點是你必須做某種身體的練習——你喜歡的練習,這點沒法商量。
身體,是你與上帝摔角的戰場;僵硬的身體,無法承受失敗的力量。
▋ 3. 藝術
練習任何一種藝術,都可以幫助你學習失敗。
在《藝術與恐懼》這本書中,有個故事:
有一位鋼琴家跟大師學習鋼琴。
有天,鋼琴家對大師說:「我很困擾,我一直覺得在腦中聽見的音樂,遠比我的手指彈出來的音樂要好聽太多了。我不知道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大師對他說:「...你憑什麼認為,這個感覺會消失?」
藝術,是一場注定失敗的活動。試圖精進自己的藝術家,就是被判了「眼高手低」的無期徒刑,你的手永遠無法做出你腦中的美好想像。
寫作,尤其是如此。
我跟鋼琴家一樣:在我腦中的文字,遠比我寫出來的文字要好太多了。我真希望我可以在腦中隨便想想,一篇美好的文章就出現。
但這不可能。甚至,「眼高手低」才是常態——論文的英文 Essay 是來自法文,原始意思是「嘗試」,我們藉由寫作,來釐清我們到底知道些什麼。
我們不是懂了才寫作,是因為寫作所以才懂了。
為了搞懂「失敗」這個概念,這篇文章我寫了足足一個禮拜,每天都花了四小時以上的時間在修改,總共改寫了七次。(還太少了。村上春樹平均改寫 10 次,海明威《戰地春夢》據說改寫了 47 次。)
但即便如此,這篇文章注定是失敗的。我永遠不可能用文字講清楚我體悟到的「失敗的力量」究竟是什麼。道可道非常道。
我更不可能決定讀者看見時,他們心中體悟又是什麼。作者已死。
甚至,在文章寫完的當下,我已經失敗了——反覆改寫一個禮拜之後,我對這個主題已經有了新的想法,我已經想乾脆整個重寫一篇文章了。
濯足入水,水非前水,文章在你寫完的當下已經死了,寫作者只能接受這點。
我聽過畫家這樣描述:一幅畫永遠沒有完成的一天,只有你停止工作的一天。寫作也是。文章永遠沒有寫完的一天,只有你停止改寫的一天。
寫作者的宿命,就是接受每一篇文章都是失敗。
但,這是好的。
失敗帶來的最大禮物:平靜與自由。
接受了「懊悔」,我不在乎結果,只看過程:改寫文章七次,就是思考自己的失敗七次,每一次都讓我更靠近我的真實。
接受了「虛無」,我不再管效率,我更在乎寫作過程本身,讓每一次修改文字,每一次思考都是一場舞蹈。
接受了「執著」,我不再被「燒毀一切」的執著阻礙。那個半夜三點對我咆哮的執著,現在是我的寫作教練:我獲得更強的寫作耐力。
失敗沒有讓我放棄目標,反而讓我獲得更大的力量,保護我不迷失在焦慮與慾望中。
這篇文章標題我寫「從懊悔、虛無與執著中找到力量」,但這其實有點誤導。我確實從失敗中找到了力量,但力量只是副產品。
面對「失敗」的第一步,恰恰就是:不要試圖精通任何東西,不要試圖獲得任何力量,只是平靜地接受失敗——即便只是失敗沒有力量,也很好。
“It’s important that a man dreams, but it is perhaps equally important that he can laugh at his own dreams.”
「有夢想很重要。而也許同樣重要的,是嘲笑自己夢想的能力。」——林語堂.《生活的藝術》
人生都是虛無,快跑不一定能贏,力壯不一定得勝,沒什麼好積極追求,沒什麼好超高效率。
執著於力量,只會像堯聖一樣卡在執著,無法超越。
真正的力量,往往來自絕望的低谷。
JK Rowling 曾經說過,如果她沒有離婚破產,靠著救濟金生活,她可能永遠寫不出哈利波特。她說:
「我被失敗解放了。我最大的恐懼實現了,但我還活著,我還有一個可愛的女兒,我有一台老老的打字機,我有一個很大的創作題材。人生的谷底,成為我堅硬的基底磐石,我在此重新鍛造了我的生命。」
練習放下對失敗的恐懼,主動與失敗做朋友吧!
失敗是人人都有的內在神祇,能帶給你真正的平靜與自由。
對,「祂」,神格。我認為人的內在是由多個神性存在組成的(紫微斗數的十四主星、希臘神話的眾神....),「失敗」也是內在神性的一種,在紫微斗數很接近煞星與化忌(aka 凶)的存在。失敗的藝術,就是學習接觸這個內在神性。
林語堂在《老子的智慧》對這段莊子的翻譯很美:「A sage lives like a partridge (without a constant abode) and he eats like a young bird (contented with what the mother bird gives him). He goes about like a bird (without definite destination) and does not declare himself. When the world is in order, he prospers along with all things, and when the world is in chaos, he cultivates his character and leads a leisurely life. After a thousand years, when he is bored with this earthly life, he becomes a fairy. Riding upon white clouds, he arrive at God’s abode. The three kinds of trouble cannot reach him and he is preserved from harm. How can he suffer from humiliation?」
這篇文章來自《曼報》曼尼曾經說過的一句話啟發:
「我只有在目標幾乎確定會失敗的情況下,我才能完全的投入做一件事,因為內心沒有對結果的執著。」(paraphrasing)
寫了一萬兩千字,只為註解這一句話。
一個真的領悟了失敗的人,會寫一篇「失敗的藝術」的文章,説説自己有多會失敗嗎?
這篇「失敗的藝術」文章寫失敗了,那我是真的很失敗,還是其實蠻成功於「失敗的藝術」?
如果我很擅長失敗,那我算是成功的人嗎?我好煩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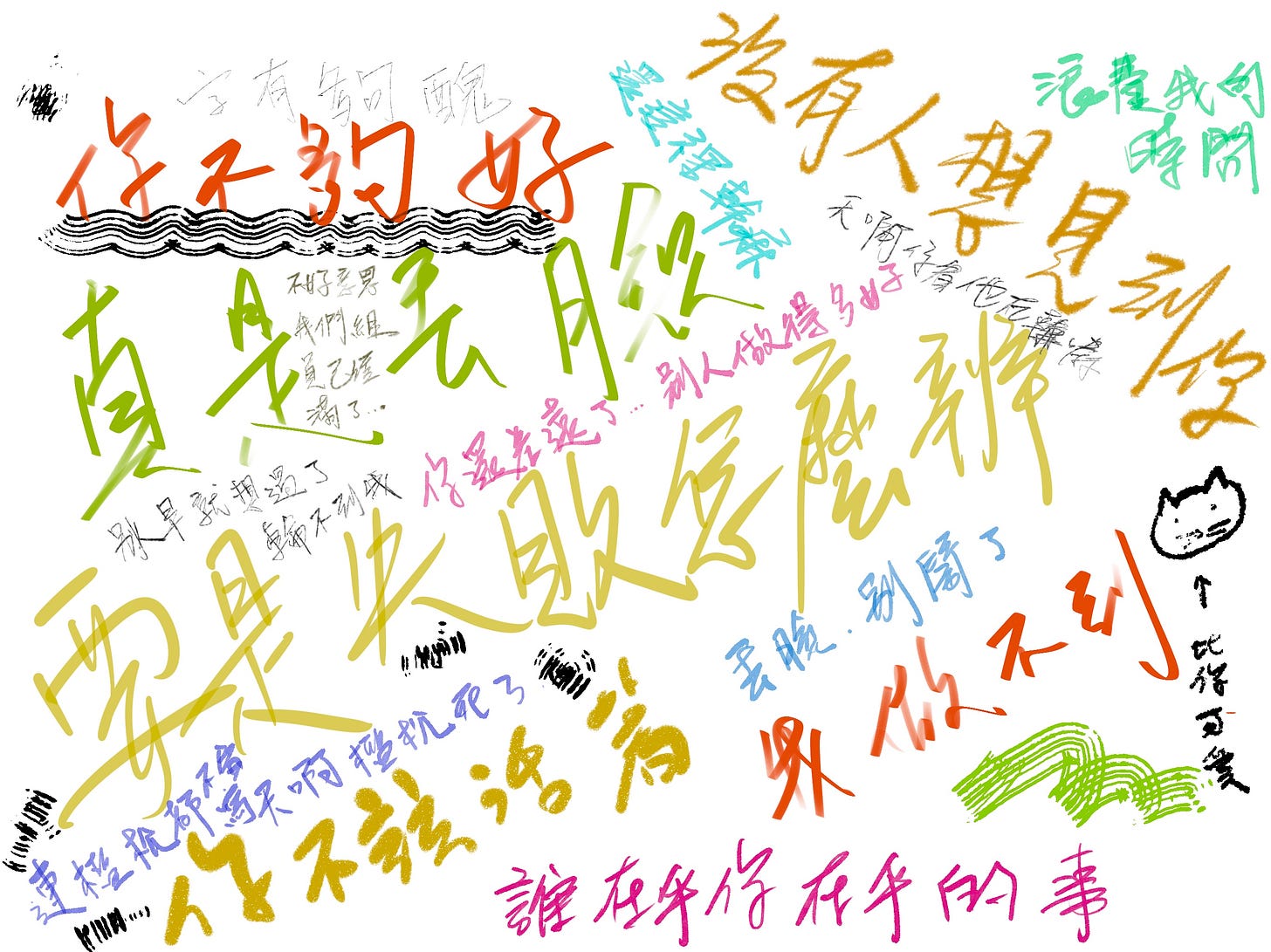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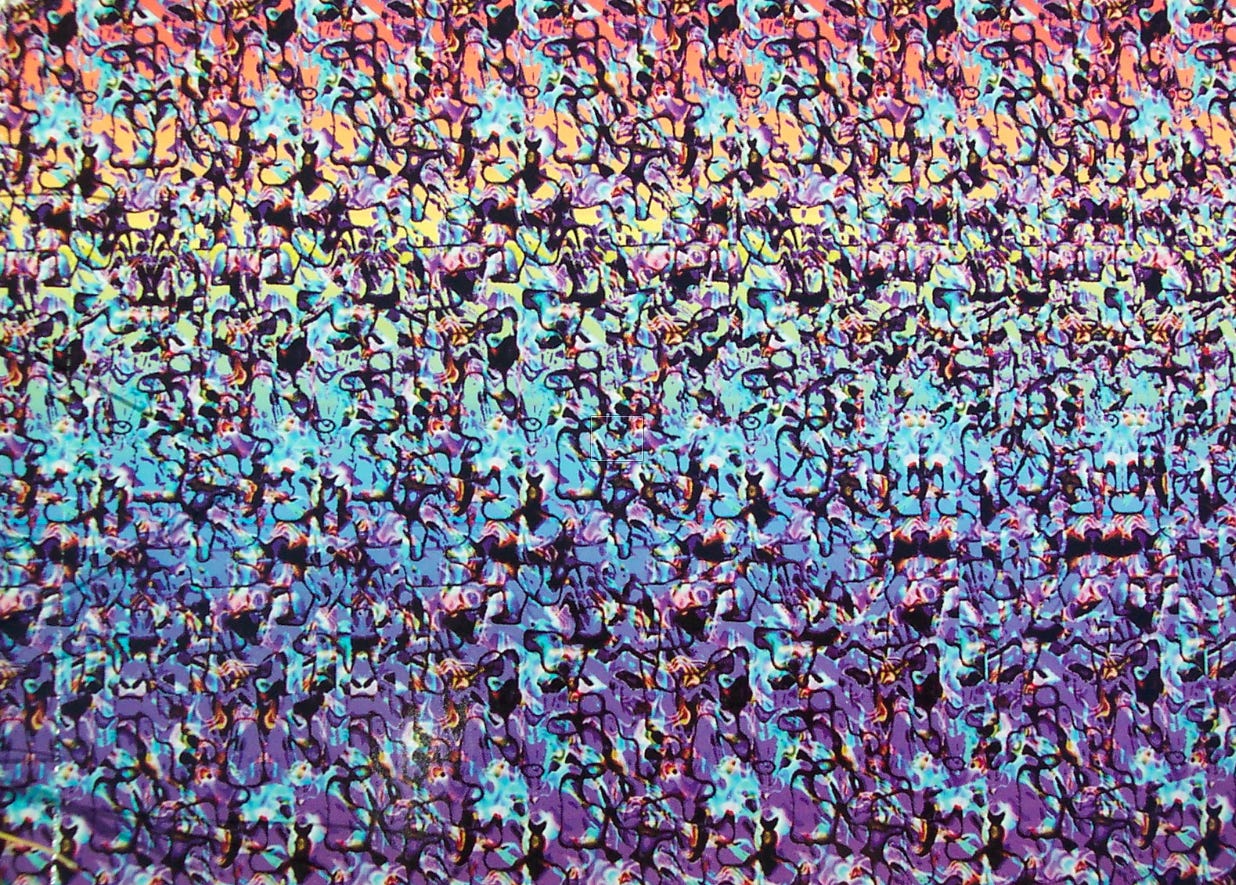
同為喜歡寫作的人對這篇非常有感觸。看到塗塗改改本身就很快樂那邊真的非常有共鳴,真的是沒有放下電腦就沒有寫完的一刻哈哈哈永遠都在修改。
有時也會懷疑這一切到底有什麼意義。只有當過程本身就是意義,無關結果的時候才能免於荒謬的折磨。想一直跳舞。
(btw 我高中三年也是用課業跟我不喜歡的社團填滿,最後考上資工才發現自己討厭寫程式)相似的令人哀傷。
也許你曾經是很正向的很行銷的,但也因為你的努力,有很多人因為你的分享帶走了一點需要的東西。我當初就是因緣際會下跟到你的用 Obsedian 卡片盒筆記法的直播,才找到最適合我的寫作工具,真的非常感謝你喔~(雖然現在寫卡片的部分還是完全失敗的哈哈管他的)
期待繼續看到你的分享,祝新年快樂:)
謝謝加恩浮出水面分享,上次看到你在喜劇節
沒想到這中間經歷那麼多(是說也很久沒留言了)
看到跳舞讓我想到陳慧琳的不如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