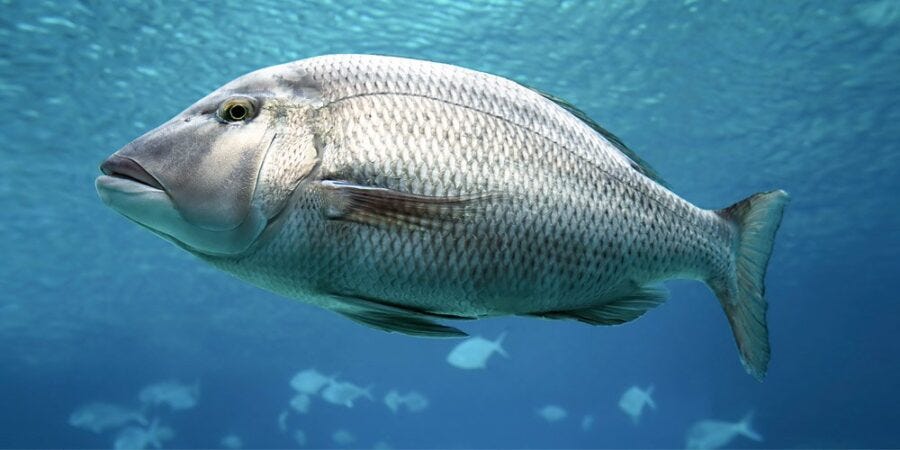「這是水」
兩條年輕的小魚一早在游泳,遇到了一條老魚。
老魚對他們兩條小魚說:「早啊兩位!今天的水感覺如何?」
小魚們沒有說話繼續前進,過了一陣子,其中一條對另一條問道:「他X的什麼是水?」
— David Foster 《這是水》
大學讀到第二年,我正處在休學邊緣。
高中畢業那年,學測成績還不錯,因為我最擅長的科系是生物跟化學,因此跑去讀生化科技系。
看起來是理所當然的選擇,大一第一次段考後,我的成績一落千丈,從此完全感覺不到讀書的意義。
畢竟,我已經對「大人們」證明了我可以考上台大。既然已經證明了,何必繼續研讀我從沒有真正喜歡過的生物和化學?
當時心想著只有一件事:「我真的要就這樣念完,去讀研究所,拿個生化碩士,在實驗室當研究人員?」
處在生命意義失重狀態下的我,誤打誤撞地開始旁聽社會學的課。
我經歷了許多第一次接觸社會學的同學會發生的事情:毀了三觀,吞下紅色藥丸,在真正的現實重新醒來,所見的世界充滿階級鬥爭、神話與意識型態。
雖然因此我進入了一段憤世忌俗的階段,但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原來同樣一個現實,可以被徹底解構,重新認識許多次。
所謂「文組」
一直到最近這幾年,才知道那個年代大家說的「文組」如歷史、社會學、語言學、文學等,在西方屬於一個歷史悠久的教育類別:「自由技藝」(Liberal Art)。
「自由技藝」起源於古希臘貴族教育,目的在於訓練你「如何思考」,好讓你免受他人奴役,成為奴役他人的貴族。(aka 第一次當老闆就上手)
自由技藝包含七種領域:
拉丁文:貴族國際通用語言
邏輯:如何想清楚
修辭:如何說服人
算術:如何管錢
幾何學:看懂建築
音樂:在樂理中理解世間法則
天文學:以占星術理解宇宙法則。
或者一句話總結:「如何思考」。
這個思考並不限於那些哈佛商學院熱門課程、策略思維等等商業上的思考,更進一步地,是對於「現實的認知」。
老魚明白自己身處於水中,而小魚們尚未理解何謂「水」的存在,這之間並沒有知識的差別,而是認知的差別。這就是自由技藝的所在。
老魚小魚故事來自美國知名小說家,David Foster 在 2005 年 Kenyon College 的畢業演講《這是水》。
這段演講,也曾經是社會系畢業演講的致詞內容。
畢業演講(commencement speech)照慣例,由一位重量級人物對那些忐忑不安的畢業生們講些鼓舞人心的雞湯,好讓他們安心上路。
David Foster 刻意避開那些雞湯,而是用專屬於小說家的精闢文字,描述年輕畢業生即將面對的殘酷挑戰:
「日常」。
大學時代的我,並未體驗過真正的「日常」(day-in day-out),讀不到他的精髓,只讀到字裡行間的小小幽默。
七年後重新讀一遍,心頭一時攫住,許久難以自己。
這封信,我試著想整理的是:重新閱讀一次 David Foster 畢業致詞《這是水》 之後,我讀出了什麼東西。
自由技藝讓你免於「大腦」的奴役
古希臘人早早就意識到一件事:即便我們並未被另一群人類奴役,我們也正在受大腦的奴役。
我們被愉悅獎賞機制所困,成為大腦邊緣系統1的僕人。
自由技藝的訓練,如同字面意義上真的是「獲得自由的技藝」,藉由訓練自己「如何思考」,擺脫大腦的控制。
這一點也不容易。
可能這一天,你剛結束12小時的輪班工程師白領工作,飢餓勞累,只想回家好好洗個澡,吃個東西,躺在沙發上追劇。
但是走出公司那一刻你想到,因為這份輪班工作,你已經一個禮拜沒有買菜,家裡只剩下冷凍庫的花椰菜米。
該死的生酮飲食。
你決定忘記生酮飲食一天,先買一杯手搖杯墊胃,一邊在擁擠的下班車潮中緩慢前進。
(我有提到你每天開車通勤三小時嗎?為了放那台 85 吋浮誇電視,你在汐止買了一間大套房,搬進去後發現因為通勤,電視沒時間看了,人生最蠢的決定。)
終於到家了,正在尋找停車位時,一台摩托車媽媽載著兩個小朋友逆向穿梭而過,你急煞,喝到一半的手搖杯灑了出來,弄得車裡和你的高級襯衫上四處都是百香烏龍加椰果微糖微冰。
這時你想到,你已經一個禮拜沒洗衣服了,這是最後一件可以穿去上班的襯衫。
車裏都是百香果的味道,肚子還是超餓,等等只能吃花椰菜米加橄欖油。
Fuck。
去你的生酮飲食。
瀕臨崩潰邊緣,你可以在車內痛罵機車上的媽媽,不負責任、死三寶、道路公共危險,自己死就算了還帶小孩一起死。
搖下車窗比中指、抓行車記錄器畫面檢舉她。
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反應,
考量到你家裡只有花椰菜米。
但是,你也可以選擇思考,也許車上的小孩已經高燒三天,現在意識模糊,這位媽媽正在緊急趕往醫院的路上。
這不是道德勸說,不是要教你「我們應該怎樣思考」,或者「好人會怎樣想」。
而只是一件單純的事實:
「我們有能力選擇怎樣思考」。
我們擁有掌控大腦的終極自由,是任何人都無法剝奪的。
作為一個宗教人
沒有人是真正的無神論者,身為「宗教人」(homo religiosus)我們都在崇拜著什麼。
不只基督徒、錫克教徒或關公乾兒子才是宗教人,狂熱於職棒、炎亞綸、獅子會、保健食品、純素生活...也是。
我們總會將某些事物「視為神聖」,進行屬於自己的崇拜。
在上帝已死的現代,最主流的崇拜是「自我」,以自拍為儀式,社群媒體為教堂,短影音為快閃讚美詩集,串連全世界數十億的信徒。
同時也金錢,權力、肉體與性吸引力、智力...等。
崇拜金錢的,永遠缺乏;崇拜肉體的,衰老時將在鏡子前死亡數萬次;崇拜權力的,永遠害怕無能的自己。
崇拜自我,這世界永遠對「我」不公,「我」永遠對世界憤怒,「我」因而永遠隔絕於世界之外,處於永遠的孤獨。
無意識崇拜的人,早已精神性死亡。
隨之而來生物體的死亡,只是遲早的事。
然而 David Foster 要強調的,不是「你應該選擇基督教而非滑抖音」這樣的道德說教。
信仰金錢、權力、肉體...都不是最危險的。
最危險的是,我們是無意識地,選擇這些崇拜。
因為「快樂」才是最高標準,誰讓我爽我就拜誰,我們聽從了大腦邊緣系統的話。
我們心中最神聖的那塊祭壇淨土,竟然毫無管制地任人踩踏,讓大腦原始的愉悅獎賞機制決定我們的信仰。
英文俗諺說: “Mind is a great servant but a terrible master.”
「大腦是極為優良的僕人,但卻是糟糕透頂的主人」。
畢竟,那些用手槍自殺的人,射擊對象就是大腦,這個糟糕的主人。
自由質問
我們時常忽略「我們有掌控大腦的終極自由」,就像小魚忽略水的存在一樣。
但即便這樣,生命還是不時會邀請我們面對這項主控權,像是彈出式視窗一樣。
我稱之為「自由質問」。
不過,自由質問不會出現在普吉島度假村、熱石按摩、或者在精釀酒吧喝酒的時候,
只有在夏天擠爆充滿汗臭的捷運車廂裡,在超市沒有盡頭的下班買菜人潮排隊裡,在那不可承受的「日常」之中,這個自由質問才在耳邊低語:
「你選擇順從身體?還是選擇思考的主控權?」
但這質問的細微氣音,總是被俗爛、噁心、低級的超市音樂轟炸淹沒。
(就是你,全聯雞巴福利熊)
這是水
選擇回應自由的質問,是無止盡的反覆訓練。
這訓練包含專注、意識和自律,包含真心在乎他人,並且在每日每夜枯燥乏味的生活中,用那些一點也不好玩的方式為他人犧牲。
在成人生活無盡的日夜重複中,我們必須不斷地提醒自己:這是水,這是水。
“This is water“ 。
令人細思極恐的是,質問不只在我們精神萎靡,肉體患難中出現,這質問也毫不留情,無得通融,甚至以生命為代價。
《這是水》演講發表三年後, David Foster 長達二十年的憂鬱症急速惡化,藥物治療無效,於 2008 年 9 月 12 日被發現在住家後院上吊死亡。
「這是水」,遂成為他迴盪在畢業禮堂的最後一句話。
最近訂閱人數剛破 100 人,謝謝各位的支持。
這個數字,也讓我不斷思考這個電子報到底要寫什麼樣的主題,畢竟我的出發點和行銷、區塊鏈、科技媒體那一類站在利基點上的經營方式不太一樣。
例如,我不知道這篇文章是否會太沈重。
同時也會想,我做喜劇表演的人,是不是應該寫些輕鬆好笑的比較對。
但說實話,這些可能有時沈重,有時怪異的內容,才是我內心最真實的自己
我並不是所謂「專業」的喜劇演員,我也不認為「專業」這種事情存在。
我能夠做的是,把「試著當喜劇演員」這趟瘋狂旅程中,當下我在學習的課題,用文字的方式分享給你。
有時這些課題是喜劇,有時是悲劇,有時什麼都不是,更像是台北車站天橋上阿伯的喃喃碎語。
因為這些是 real 的。
但同時我明白,拿來閱讀的可能是你的上班時間,也可能是你寶貴的休息時間;你選擇打開電子報,是我們之間的默契。
而我珍惜這樣的默契。
我不希望《書不起》變成我的個版,讓「真實」變成我情緒發洩的藉口,塞在你那個本來就已經充滿垃圾信件的收件夾裡。
(說說看你的收件夾現在有幾封未讀啊?呵呵)
在真實性與文筆流暢、有料之間,我會盡力取得一個平衡,這是我珍惜我們的默契,所能夠給你的承諾
如果你讀完有任何想法或反饋,隨時可以寄信、留言、或甚至用 Instagram 和我對話。
或者,你也可以分享我的文章,讓更多人一起來取暖。
(原來是 CTA 的部分)
前面還是很真心寫的啦。恩。
獎賞機制主要腦區,又稱為爬蟲腦,大腦中最原始的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