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與「自我」和平相處
讀《The Inner Game of Tennis》:「放鬆地專注」的藝術
上週寫完「原來我對學習的理解,全都是錯的」文章之後,如同結尾說的:
「方法技巧都有用,但真正的問題是『方法都擺在那邊,我就是做不到』。
這意味著,除了這些方法以外,應該有更底層的『元技能』是能幫助你超速學習的關鍵。」
這些「元技能」是什麼?這週我整理了之前的筆記,針對這個主題進一步思考,我認為可以分成三類:
1. 克服恐懼的技術
2. 克服羞愧感的技術
3. 在壓力下放鬆的技術
剛剛好,上週文章出來之後,讀者推薦我讀一本書《The Inner Game of Tennis》,我讀了之後驚為天人——這本書完全就是在講「在壓力下放鬆專注的技術」。
這本書作者 Timothy Gallwey 哈佛大學畢業,主修英國文學,生涯中做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網球教練。在 1970 年代他受到東方思想影響,開始把禪宗的「無心」的概念應用在網球訓練裡面。
然後他發現,使用這套方法的學生,都在短時間內產生顯著的進步。他們動作更流暢,且練習過程更輕鬆而沒有挫折情緒了。
我覺得這是這本書最厲害的地方:Gallwey 把球場作為實驗場,直接應用禪宗的思想在網球訓練裡面。
這讓所謂的「禪」就不再是玄乎妙乎的東西,而是可以不斷複製、修改細節,變成一套實際方法論的技巧,一套「放鬆地專注的技術」。
而這本書,就是這套技巧的實驗結果。
這本書出版之後,Gallwey 發現他的讀者大部分都不是打網球的:CEO 把這套技術應用在決策、音樂家用來解決舞台焦慮、各領域運動員都採用到比賽....因此,他還繼續寫了「The Inner Game of 滑雪、音樂、工作」等多領域的書。
Gallwey:「放鬆地專注,是最重要的藝術,因為所有的藝術都需要這項底層技能。」
這本書,我想跟你分享的是:
放鬆的藝術:用大腦刻意努力,反而會有反效果。
相信你的身體知道怎樣做:你的身體是一場工程奇蹟
像是裁判一樣單純觀察
不用刻意讚美自己:讚美只是批評的偽裝
Inner Game 就是所謂的「修行」:回歸本心的藝術
(全文五千字,閱讀時間十分鐘)
▋ 放鬆的藝術:用大腦刻意努力,反而會有反效果。
在網球教學的傳統方法,教練會點出學生的動作缺點,例如「太晚拉拍」,然後學生就要記得「早一點拉拍」,練習改進。
聽起來沒有問題,對吧?我們從小到大不都是這樣學習的嗎?
Gallwey 不滿意這種教學方法。
他發現,當學生試圖告訴自己「早一點拉拍,早一點拉拍...」的時候,往往身體會更加緊繃,練習過程會充滿挫折(做不到就會怪罪自己),而且效果很差,總是要花很長的時間才改得過來(如果真的有改成功的話)。
他想要找到不同的一套方式來教學生打球。這次,他不做任何技巧講解,只是先打十次正拍,讓學生自己觀察他的動作。
他的學生觀察之後,做出一個評論:「啊,所以擊球的時候要移動腳步!」
然後,學生自己打了一次球,所有的姿勢都完美:重心前移、球拍高度、流暢,打完自然而然把球拍舉過肩膀....
只有一個問題:他沒有移動腳步。
這點非常有趣:他唯一用「意識腦」注意到的地方,就是他唯一沒有做到的地方。
像這樣的案例發生太多次了,Gallwey 於是做出了兩個結論。
第一個是「畫面遠勝於言語,直接展示遠勝於教學」(就是所謂 show, don’t tell),太多的口頭指引比完全不講解更糟糕。
第二個則是「不要太努力」。太用力做一件事,太認真做一件事,往往會帶來反效果。(很像我們常說的認真就輸了。)
如同鈴木大拙禪師在《 Zen In The Art of Archery 》序言說的:
「每當我們反思、刻意、概念化,原本的無意識腦就消失了,想法就介入了。箭是射出去了,但是沒有飛向目標,目標也沒有在原地不動...
人類總愛思考,但只有在不思考,不計算的時候,才可以拿出最好的表現。」
Gallwey 也提出一個觀念:我們其實是由「兩種自我」構成的。
「自我一」掌管意識腦,負責理性思考、分析,與「自我」(ego)綁定。當我們過度努力想要做一件事的時候,就是「自我一」在作動。
「自我二」掌管無意識腦,負責身體的動作、靈感啟發與繆思。我們真正的學習,其實都是「自我二」在做的,但是我們無法用語言描述這個過程。
你可能有那種「小時候莫名其妙就學會了一件事」,或者更小的時候學走路、學母語或外語都更快...因為小孩的心靈還沒有被社會化,「自我一」還不太會干預「自我二」,所以可以學的很快。
反過來說,球場上的球員動作問題,幾乎都有一樣的特徵:「自我一」不相信「自我二」,於是撈過界來試圖幫自我二做事情。所以你會觀察到球員的嘴角變得緊繃、身體僵硬、挫折情緒越來越濃...都是效率很低的學習。
然而,當球員的「自我一」真的安靜下來,不要刻意操控自己的身體,只是讓「自我二」自然做出動作,他們往往會有非常流暢的表現。
所以,怎樣做到這件事?怎樣讓「自我一」安靜下來?
▋ 相信你的身體知道怎樣做。
第一個做法是「相信你的身體」。
身體是精妙到超乎人類想像的工程奇蹟。我們已經可以穩定把人送上太空,但是仍然做不出一個機器人來做簡單的洗碗掃地。
每個人,都擁有這個精妙的生物奇蹟。你的身體裡面已經具有幾億年演化之後的智慧,你必須相信這點,甚至是以一種「敬畏」的心態來看待。
「相信你的身體」(Trust Thyself),在球場上不代表「相信自己會贏」,而是相信你的身體知道怎樣做,你不需要做過多的控制,你只要「讓」這一切發生。
這裡的關鍵字是「讓」(let)。
這很像是「家長放手讓小孩自由發揮」的過程,你的身體仍然會犯錯,但你信任你的身體會自己學習,自己成長。
所以重點是「讓」它發生,而非「使」它發生——let it happen, instead of make it happen。
這世界上幾乎每個小孩都自己學會了走路,沒有家長會在旁邊教小孩「重心要怎樣轉移」
媽媽也不會因為小孩跌倒了就罵他,只是單純觀察,簡單鼓勵而已。
媽媽也不會因為小孩跌倒,就覺得自己是很糟糕的媽媽,媽媽的自我認同不綁在小孩身上。
「自我一」和「自我二」的關係應該要像這樣,你單純用愛與觀察對待自己,你的兩個自我,是兩個獨立的個體。
我認為在這個點上,詮釋得最好的是聖經:
「神用神的形象造人」——《創世記》1:27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箴言》9:10
既然身體是神的形象而造的,學會敬畏你的身體的能力,相信你的身體,你就會開始掌握「身體的內在智慧」。
作者也說,你越是相信你的身體,你也會越得到真正的自信——因為你知道你做得到,你的身體做得到。
自信缺乏,恰恰就是「自我一」試圖掌控,不斷自我批評下的產物。
▋ 像是裁判一樣單純觀察
完全放下「是非判斷」的念頭。
自我一最擅長的功能,就是自我批評。但是自我批評、罪惡感、愧疚感...這些都對學習沒有任何幫助,只會讓你身體越來越僵硬。
Gallwey 提出來的方法是,像是裁判一樣單純地觀察——裁判不在乎誰得分,裁判只在乎單純中性的事實。
如果球打得不好,不用去批評自己打得不好,只是單純帶有一點興趣的態度,像是科學家觀察實驗結果一樣,觀察:「啊,這顆球出界了。有趣。」
有個學生來找作者,說自己的反拍總是太高,已經有至少五個教練都跟他說反拍太高了,可是他都改不掉。
作者沒有多做什麼,只是請他先揮幾次——確實太高了。
作者什麼也沒有說,只是請學生到一個大窗戶前面揮拍,觀察自己在鏡子前面的反設。然後學生自己驚訝發現——反拍真的太高了!
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這個學生已經被講五次以上了,但是他必須自己親眼看到,他才真的「知道」這件事。
他總是「概念上知道」,但沒有真正地「看見」。
在這之後,作者帶學生到球場,餵球給他練習。現在學生因為真的看見了自己的問題,短短十分鐘內,他的反拍問題完全解決,流暢到像是天生就是用正確的姿勢打球一樣。
學生:「當我清楚看到我哪裡犯錯了,我的動作好像就自己改進了。」
作者:「他確實學會了,但他是否有被『教會』?這始終是讓我不斷思考的問題。我無法形容當下的感覺有多美妙,我幾乎快哭了。我學到了一課,他也學到了一課,但沒有人是老師。」(I had learned and he had learned, but there was no one to take the credit.)
當你使用是非判斷、語言、意識腦刻意地要去改正動作,幾乎都不會有好的效果。自我批判會導致情緒,情緒導致肌肉緊繃,肌肉緊繃導致無法做出良好動作。焦慮都是從這裡來的。
但如果你可以放鬆,只是中性地觀察,你的身體自然而然就會做出調整。作者:「進步,始於你如實地接受每一次擊球。」(The first step is to see your strokes as they are. )
怎樣更好地做這個觀察?
作者會找一些特定的「錨定點」讓學生去觀察。
例如「球的縫線」——要在高速轉動的球體上看見縫線,你必須非常非常專注。
你也可以專注觀察球拍的位置——隨時知道球拍在哪裡是成功擊球的關鍵。
你也可以專注觀察身體的感受,不同肌肉的張力——例如三頭肌的張力會跟你的拍子高度有關係。(或者在拳擊裡面,髖部的旋轉跟你的出拳力量有關係)
你也可以專注在比賽的節奏。你沒辦法強迫自己有節奏,但你可以專注在節奏上,幫助他自然發生。
重點是:不要硬逼自己專注。(Natural focus occurs when the mind is interested. )
而是,「對球保持興趣」。只有興趣,可以真的從內心引導出專注。
不要預設你已經知道球的一切,不管你人生中看過多少顆球了,永遠不要預設你已經知道一切了。帶著幾乎一片空白的心思去看見球。觀察球的縫線、動態、飛過網子時有多高、擊球的聲音怎樣不同...
練習這樣的觀察,「自我一」批判的聲音會越來越小聲,你也越可以專注。
▋ 不用讚美自己:讚美只是批評的偽裝
前面講到,「自我批評」對於學習沒有幫助。
那可是,正面思考、自我讚美呢?這樣是否就有用了?
作者的經驗指出:一樣沒用。
他曾經一次教三個學生,第一個學生有幾顆球打得很好,他就順口稱讚了。但後來,幾乎每個學生的表現都變差了。
他發現問題是在於:一但教練做出了讚美,引入了正面思考,學生就會開始判斷「什麼是好的」。
如果有一個動作是「好」的,學生就會想要追求那個「好」,於是「自我一」又會開始作動,肌肉就又緊繃了。
從這個角度上看,讚美跟批評是一樣的。都會讓「對/錯」的天平再次出現。你又繼續被「打分數」。
讚美只是批評的偽裝,兩者都是「自我一」試圖操控你的行為。
為了要達到「無心」的狀態,你得完全放下是非判斷,如實地看見事情的本身(as is)。
▋ Inner Game 就是「修行」:回歸本心的藝術
我越讀越覺得,這書名《The Inner Game of Tennis》,這個「Inner Game」有一個非常貼切的中文翻譯:
「修行」。
我們過去都把「修行」看得很玄很謎,這本書最屌的地方就是,作者用運動訓練,把「修行」給除魅了。
這點給我一個全新的啟發。當你拿掉「修行」表象的那些怪力亂神、充滿宗教色彩的東西之後,你會發現「修行」是一個很單純的事情:忘記。
我們從小到大社會化過程中學到了太多雜七雜八的觀念了,這些觀念都會影響我們更輕鬆平靜地活著。
現在,我們只是練習把它放掉,練習忘記。
這就是修行:忘掉那些「阻礙你成為你自己」的心理習慣,回歸本心。
第一個要放掉的就是「價值判斷」,放掉「是非心」,不去在意一件事是好是壞。
當你學會不要去判斷好壞,「自我批判」的聲音就會越來越小聲,然後自己就會越來越不被影響,於是越可以專注,讓你的潛能真正開展。
我很喜歡作者的比喻:
當我們種下一株玫瑰的種子,我們不會去批評這個種子「太小了,根本沒有花!」,我們只是如實地看待它。
種子沒有好或壞,就只是一顆種子。
當玫瑰發芽了,我們不會批評它「太嫩了,根本不是玫瑰!」
發芽沒有好或壞,就只是發芽。
當玫瑰長出枝幹了,我們不會批評它「只有枝幹,怎麼沒有花!」
枝幹沒有好壞,就只是枝幹。
我們只是靜靜地觀察玫瑰生長的過程,給予足夠的環境與養分,讓它自己長成一株玫瑰。
這個道理,在各個領域都不斷出現:聖經說「不要論斷」,佛家說放下執著,儒家說中庸...
描述最貼切的,應該是禪宗的「無心」:
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
因為「無心」,所以完全專注。
因為完全專注,所以發揮身體最大潛能。
於是,你就達到了西方說的「peak performance」(巔峰表現),
或者東方說的「禪」,如庖丁解牛一樣,收放自如,行雲流水。
大概這樣。
讀這本書,我只有一個感覺:扼腕到爆。
明明是 1974 年就出版的書,竟然到了 2025 年,整整將近五十年了,這些概念還沒有普及。這真的非常弔詭。
如果你可以掌握這些概念,搭配上一本《Make It Stick》的學習方法,你學習新技能的能力會馬上超越其他人一大截。
但也許沒有普及也是有原因的。這篇文真的是我試圖寫過,最難講清楚的主題了。強力推薦你去讀原書,每個人會有不同的啟發。
這本書的觀念,真的是底層邏輯,應用在幾乎一切的領域上:
我在寫文章的時候,也很常感受到那個「自我一」消融,剩下的只有螢幕與我的手指,以及文字本身的聲音(我是用聲音寫作的)
而我反思過去作喜劇,我到底是怎樣學會寫笑話的?其實根本不是我在學習,而是「自我二」在學習,我只是單純好好地觀察「笑話」。我的經驗是:任何過度分析笑話的嘗試都是反效果的
在人際關係上,我發現當我不去標記這個人是「好的還是壞的」,而是單純地「觀察」,我可以更中性地傾聽,認識他人。
不起分別,不加造作,如實認識,於是解放自己。
理解這點,我在生活上也不那麼努力「硬幹」了。
最近,我在練習「不那麼努力」的技巧,只把努力用在「讓自己進入專注」的階段,接下來就由身體接手。
「放下是非判斷」的練習,尤其對焦慮特別有幫助——當焦慮出現時,我會刻意找一個觀察點(通常是我的呼吸、身體感受、或者想法本身),
然後放下那些「刻意追求什麼」的念頭。
這樣有用嗎?這樣會讓我的成就更高嗎?我的表現會更超人一等嗎?
我不知道。
但至少,我現在的內心是更平靜舒坦一點,比較可以快樂了。
這本書幫助我最近跨過一個很大的坎,希望這篇文章對你有些幫助。
補充:我延伸寫了一篇文章,是書中提到的「自然學習法」的操作細節,可以到我的臉書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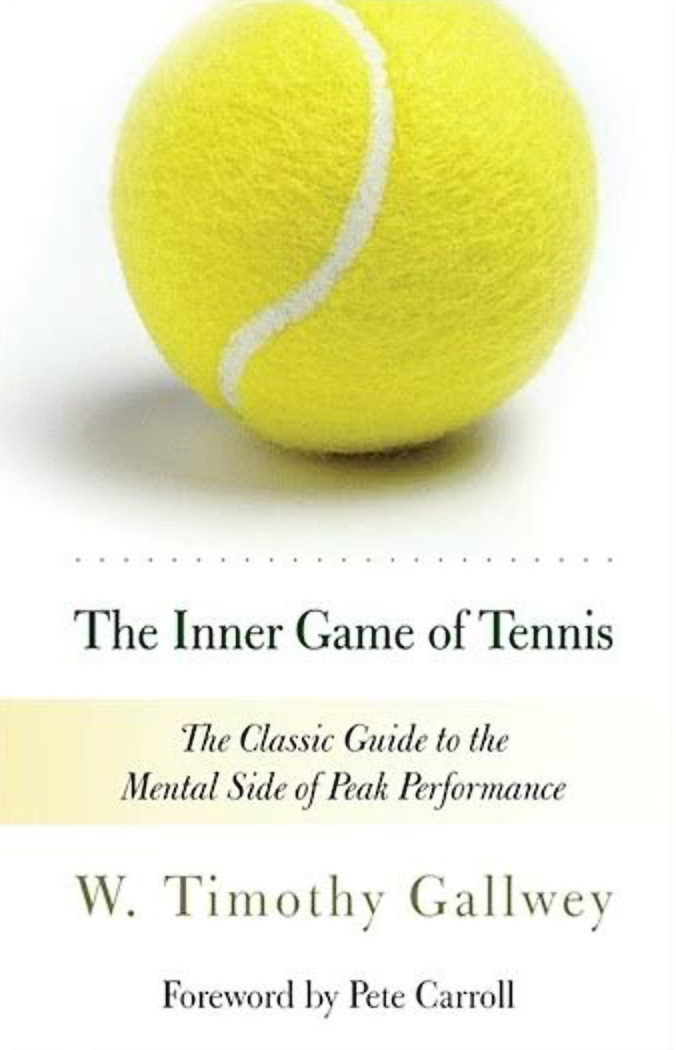

看完你的文章讓我想起前陣子看到的一則短文,在探討how to avoid the trap of self improvement,裡面也有提到要脫離焦慮迴圈的方式就是得放慢腳步、練習自我接納、專注當下。但看了你的文章之後又覺得整個概念更完整了~真好!謝謝你的整理真的很喜歡~
聯想到「自我二」有點像自由書寫的感覺,本來如果思考要寫什麼就會開始寫不出來,但如果完全交給身體感受,就會開始文思泉湧xd 也會寫出一些意想不到的體悟。
好奇作者有無提到具體練習的步驟做法?
看到這個概念也有點類似「鬆綁你的焦慮習慣」這本書,作者不是引導大家思考而是透過練習用好奇心觀察各種生活中的迴圈習慣並記錄下來,去調整大腦應該獎勵學習的感受與行為,有提到實際作法與需要觀察的面向。但其實一剛開始練習時真的會遇到「自我一」的批判情況,剛好看到文章可以兩者一起合併練習蠻有趣的
(*記錄模板英文參考資料:https://drjud.com/mapmyha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