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的詛咒
為什麼產品會失敗,教授不會教書,人生這麼困難?(全文 6000 字)
為什麼產品定價這麼難?
為什麼教授上課都讓人聽不懂?
為什麼說明書寫得這麼複雜,直接告訴我按哪裡開機不行嗎?
為什麼不能好好說話?
為什麼人生這麼困難?
這些生活中的無數挫折,過去我以為是人的能力、溝通技巧的問題。
但最近,我讀了哈佛大學語言學家 Steven Pinker 的書《The Sense of Style》,才發現,答案可能在於一個極為普遍,但我們很少察覺的認知盲點上。
「知識的詛咒」
這個認知盲點,遠遠不只是讓教授講課難懂而已,而是在我們的生活中,處處都在影響我們的思考、決策、團隊溝通、產品設計、創業,甚至是我們對自我價值的判斷。
Pinker 在書中說:
「當你把你每天都要遇到的這類挫折乘上數十億人口,你就知道『知識的詛咒』是人類文明發展極大的障礙,效力等同貪腐、流行病和熵增。」
這篇文,是我深入讀完 Pinker 書中章節之後,我對「知識的詛咒」的概念整理,包含:
知識的詛咒如何運作?
「知識詛咒」的三種場景
如何克服知識的詛咒?
「樣樣通,樣樣鬆」其實是好事。
我們還有 AI
好好利用 AI 的「平庸性」
▋ 知識的詛咒如何運作?
一個經典的實驗案例,是史丹佛大學在 1990 年的一個實驗:「敲擊者與聽眾」(Tappers and Listeners)。
實驗中,參與者被分成兩組:「敲擊者」(tappers)和「聽眾」(listeners)。
「敲擊者」的任務是,選一首所有人都聽過的老歌(例如《生日快樂》、《Jingle Bells》),然後用手指在桌上把歌曲的節奏敲給聽眾聽。
聽眾的任務,就是根據敲擊者敲出的節奏,猜出是哪一首歌。
大概像是:看一個人在打太鼓達人,但你不能聽音樂跟看螢幕,你要猜出他在打哪一首歌。
在開始之前,研究者請「敲擊者」預測聽眾猜對的機率。
「敲擊者」們普遍預測,成功率大概會是 50%。
然而,實驗的實際結果:在總共 120 次的嘗試中,聽眾只成功猜對了 3 次。
聽眾的成功率僅僅為 2.5%,遠遠低於敲擊者預測的 50%。
這就是「知識的詛咒」:當敲擊者在敲打節奏時,他們的腦中正播放著那首歌的旋律、歌詞、和聲,他們「聽得到」整首歌。
但對於聽眾來說,他們接收到的資訊就只是一連串「嗒、嗒、嗒」的無意義敲擊聲。
當我們擁有一項知識,我們注定難以想像「不擁有這項知識的生活」,我們也更傾向於認為其他人都有這些知識,因此形成盲點。
(這也能解釋比手畫腳:比的人都覺得已經很清楚了,但猜的人永遠猜不出來。)
▋「知識詛咒」的三種場景
「知識的詛咒」在我們的生活中,四處都存在,你幾乎每天都要體驗一次。
⇨ 1. 最基本款的知識詛咒,是「教書」。
我們應該都很清楚:不是每個老師都會教書,「擁有專業知識」跟「傳遞專業知識」兩者是完全不同的技能。(在大學尤其如此)
知識的詛咒最知名的案例,就是愛因斯坦:超級會研究,但是他上的課完全沒有人聽得懂。
據說他上課時,幾乎不是在對聽眾說話,而是自顧自地盯著黑板,隨手寫下一串長長複雜的張量方程式(Tensor Equations),自言自語:「從這裡,很顯然地...」
才說完「很顯然地」,就馬上推導出另一個更複雜抽象的方程式,一跳就跳過了五、六個關鍵的數學推導。
台下的聽眾已經是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高材生中的高材生,仍然完全聽不懂他在說什麼。
因為知識的詛咒,人類史上最聰明的頭腦,也同時是人類史上最糟糕的老師。
⇨ 2. 另一款知識的詛咒,在網站 UX 設計/產品說明書上。
例如最經典的失敗案例,報稅。
作為一個報稅者,我只想知道「台灣政府要收我錢沒關係,所以我要去哪裡繳這筆錢?」
我看了一早上看不懂。最後我拜託報稅神人我老婆,她崩潰了一下午,最後終於搞定了。
(中間還出現了陷阱題,當你填寫完所有資料,走過三道驗證手續之後,你要下載某個文件才能繼續
——但是當你點擊下載,你會直接被導向新的頁面,所有填寫好的資料被清空。強,真的太強了。)
報稅這件事,是「知識的詛咒」徹底的展現。
因為其實,整件事不過就是:「我賺了錢,國家保護我安心賺錢,所以國家要抽成。我要繳錢」對吧?
真正在流動的資訊,政府只需要知道:
你是誰?
你賺了多少錢?
--> 計算完成,請你繳 {這個數量},在 {金流平台/銀行戶頭} 繳錢。
簡單幾個步驟可以搞定的事情,卻要延伸出N個專有名詞(稅籍登記、制度介紹、申報窗口、新制新聞稿、制度查詢),然後再設計懶人包、諮詢窗口...
因為設計者「知道了太多行政體系結構,深陷在知識的詛咒裡面,無法想像一般使用者的觀點」。
(當然也有防止逃漏稅的設計,但完全沒有必要搞這麼複雜吧!)
⇨ 3. 知識的詛咒也展現在「商品定價/談判」上。
其實最早提出「知識的詛咒」這個字的人,不是教育學者,而是經濟學家。(註一)
因為他們發現,買賣是一個「資訊不對等」的關係:賣家對產品了解得多,買家對產品了解得少。
理論上來說,賣家應該要可以運用手上大量的資訊,在談判中掌握更好的地位。
但事實上剛好相反:賣家會因為「知道得太多」,反而無法換位思考買家的觀點,這使得他們反而處於劣勢,無法準確預測對手的行為。
⇨ 最常見的情況是「高估」。
例如,一個軟體工程師花了兩年時間開發出數據分析工具,
他知道背後的演算法有多麼優雅、程式碼架構多麼有擴展性、伺服器響應速度比競品快了 50 毫秒、而且能夠處理比對手多一倍的併發請求。
當他向一位潛在的客戶(一位行銷總監)報價時,提出價格 50 萬台幣。
他內心的依據是:「我這套系統的技術領先業界兩年,光是這些研發演算法的成本就不止這個價錢了。」
但,行銷總監才不在乎三小演算法。
他只關心一件事:「這個工具能幫我提升多少廣告投報率?操作介面會不會很複雜?導入需要花多久時間?」
當他聽到工程師一直說演算法多屌,擴展性多好...他腦中只會想:
「太複雜,太貴。競品工具只要 20 萬。」
工程師因為知道得太多,「高估」了自己產品在對手眼中的定價,因此無法做出最正確的定價價格。
⇨ 另一個場景則是「低估」,這點是個人創業者第一次定價很容易面臨的問題。
例如我做《電馭寫作》的時候,我一開始訂的價格其實是 500 美金,遠低於我後來開出來的第一波啟售價 888 美金。
後來,我收到 Justin Welsh 的電子報。
他說,他在事業上最重要的突破,就是他定出一個「說出來聲音會發抖的價格」。
過去,他的諮詢顧問服務是每小時 250 美金,收費已經很高了,客源非常穩定,但對象都是一些基礎的工作者(都是大公司送來培訓的),他要長回答一些很無聊的基礎問題。
他思考過後認為,他應該要提高價格,才能直接訓練 CEO 等級的人,他才能開始處理有意義的、好玩的挑戰。
所以,他決定把他的顧問服務價格翻七倍,從原本的一小時 250 美金,提升到每個月 14,400 美金,8 小時。
他事先練習了幾週,每天對他老婆說他的定價,甚至在他的辦公室貼上一個寫著 「14.4K」的便利貼。
但當他真的對一位 CEO 提這個數字的時候,他的聲音還是抖得像是要告白的國中生。
「我的策略顧問方案是.....一萬四千四百美金,一個月提供八小時的諮詢服務。」
說完,對方 CEO 沈默了一陣子,Justin 滿臉通紅死死看著鏡頭,假裝鎮定。
最後 CEO 說:「就這樣?那,我們什麼時候開始?」
到這一刻,Justin 才意識到,過去他對自己的定價真的太低了。他成功打破了一次「知識的詛咒」。
看完這封 Justin Welsh 電子報之後,我思考掙扎了好幾天,也決定心一橫,把第一波售價改成 888 美金。
我沒有翻上七倍,但我打這個數字的時候,手也在發抖。
我一直覺得自己不值這個價錢。
我一直覺得我會被市場鄙視,第一波銷售可能根本沒有人會買。
我一直覺得「幹,大家應該早就會用 AI 寫作了吧,我這個課程真的有價值嗎。」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了太多「我的不足之處」:我知道真正很強的課程產品長什麼樣子,再回頭看看我正在打磨的半成品,我真的很想掐死我自己。
但問題是,買家並不知道。
買家並不是做過一輪完整市場調查、競爭者研究分析、研究完所有 AI 寫作技術的人,(如果是就不會是買家了)
買家只是帶著問題希望被解決的人。
對買家來說,只要解決問題的價值遠超過 888 美金,他就願意買課。
即便我理性知道這個道理,上市測試也證實願意付這個價錢的人是多的,當我真的要開出這個價格的時候,還是得要克服超大量的心理阻力。
兩種定價的案例,高估的工程師要克服的是「自尊」,低估的線上課開發者要克服的則是「冒牌者症候群」。
這,真的是一種「詛咒」。
從小,大人就會跟我們說「知識就是力量」,但現實是:
「擁有大量的知識並不永遠是好事。」
人是會被知識給困住的。
你知道得越多,你就越難以克服自己的「知識債」。
▋ 如何克服知識的詛咒?
「知識的詛咒」存在於個人的盲點,且時常結合心理機制(工程師對技術的愛/創業者冒牌者症候群/愛因斯坦的跳躍思考)反過來限制你,
因此,單單「試圖換位思考」真的效果有限。
Steven Pinker 在《The Sense of Style》書中,舉出了一些解決辦法
⇨ 1. 拒絕使用縮寫、專業術語、行話、黑話
有些專業術語、縮寫可能有拓展到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但知識的詛咒會讓你高估這些字的普及程度。
如果你必須放上專業術語,請簡單解釋之。
⇨ 2. 永遠要舉例子
一個沒有例子的解釋,就基本上等於沒有解釋。
有時最好放上兩個例子,讓複雜概念最清晰。
⇨ 3. 想像對方就是自己,但不知道脈絡
你的讀者分佈注定是鐘形曲線,不管你怎樣說,一定會讓部分的人覺得無聊,部分人覺得太難。
那你應該要往「更簡單」的方向去思考你要做的內容(文章、產品、書、說明書、報稅網站...),還是要往「更困難」的方向?
Pinker 建議永遠往「更簡單」的方向。
因為「知識的詛咒」,你注定會高估讀者的水平,所以最好把內容寫得「你自己覺得有點太簡單了」。
把那些你自己已經模組化、抽象化的思考拆開來,回到具體的層次,講清楚給讀者聽。
Pinker 說:「關鍵在於,把你的讀者當作跟你一樣聰明的人,但是他們剛好對於你知道的東西一無所知。」
⇨ 4. 把你的文字給一個普通人看
Pinker 認為,我們永遠會高估「自己有多了解讀者」這件事。
想想前面「敲擊者與聽眾」實驗案例,以及知識詛咒運作的邏輯:我們會把「自己對他人想法的想像」放到自己的大腦,然後以為自己知道了一切。
「這應該很簡單吧?任何人都會吧?」
實際上,幾乎永遠不是這樣。
你越是一個領域的專家,你眼中的「這應該很簡單吧」,對新手根本是有如登天。
要克服這點,你能做的就是:實際找一個對象來「對答案」。
例如,我非常提倡任何一個寫作者,都找一個身邊的人,把自己的文章不停拿去給他們看。
尤其,你最好讓他們在你面前看,觀察他們讀到哪個段落,會露出怎樣的表情。
只有這樣做,你會獲得最精準的回饋。
⇨ 5. 過一陣子再回來看
就是最常聽到的「文章要放一晚,再回來重新編輯」。
這個目的是讓大腦的短期記憶消除,你會更有機會從「讀者的角度」重看一次自己的文章。
這樣做很有用。以寫文章為例,通常寫文的當下你都會跟當下的靈感處於「熱戀期」,你必須冷靜個兩三天之後,你回來看自己的文章才能做中性的判斷。
文章以外,任何產品也都是如此。
如果沒有辦法讓一天再回來的時間,我至少會去散個步,或者打個電動再回到文章上。
▋「樣樣通,樣樣鬆」其實是好事。
Pinker 上面的建議,是專門給寫作者的,傳遞知識過程要克服的知識詛咒。
但在日常個人學習上,我覺得也應該時時記得「知識的詛咒」這個概念。
日常生活裡,什麼叫做「知識的詛咒」?
最經典的是這句話:「當你手上拿著錘子,看什麼都是釘子。」
當你太過於熟悉錘子的工作視角,你就被這個視角給侷限了,看不見全貌。
以前會非常擔心自己讀書忘記裡面的內容,強迫自己一定要把所有重點都記下來。
但隨著筆記庫逐漸成長,我發現:把所有重點都記下來,這些知識反而是一種「負債」,不是「資產」。
因為當我選擇記下所有重點,注定有很多是我「無感」的筆記。
而這時候管理筆記盒,就是處理一堆我無感的資訊。那就變成是一個辛苦的工作了,而且我也不知道記得這些事要幹嘛——這些資訊對我沒有意義,那再怎樣看似重要,也只是雜訊。
而現在,我對於「忘記」也更加釋懷了。現在讀一本書,如果真的忘了大部分,或者只做了幾張筆記,沒有整本整理下來,也不會覺得怎麼樣。
畢竟,我曾經因為把所有東西全部記下來,結果卡片筆記盒負債累累,差點要整個筆記盒燒掉重來的。
要時時提醒自己:知識很有可能一不小心,就從「資產」轉變成「負債」。
現在我的閱讀習慣,反而更喜歡從每個來源都只拿一點,但是保持我閱讀的材料非常豐富多樣化。這樣時常會產生「意想不到的連結」。
例如,我在思考「創作者的商業模式」的時候,剛好正在讀到 Steven Pinker 另一本書《Enlightment Now》,裡面提到亞當斯密認為「產品、服務與想法」的交流,是經濟發展的動力。
我延伸把這點拿去跟 AI 對話,才發現: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到一種社會專業分工,叫做「觀察的人」(The men of speculation)
他們的工作,就是不要工作,在旁邊好好地觀察人們工作的樣子,思考怎樣改良現在的生產效率。
我看了心想:這不就是現在的「創作者/知識工作者」最好的寫照嗎?
原來「創作者」的社會功能,在工業革命時代就出現了!(你當然要延伸到蘇格拉底也是可以,但我覺得那個年代的社會分工跟現代差太遠了)
於是我分析創作者的商業視角,直接因為亞當斯密而有全新的啟發。這絕對不是我讀任何一個自媒體經營大神的書,可以獲得的連結。
除了知識本身,在技術上尤其是如此。
工具技能是一種資產,但同時也是一種負債。
我時常覺得我太擅長於寫作了,以至於我在分析內容時,都只看見「文字內容」、「文字策略」,而不是一個創作者經營個人品牌的「全貌」(短影音、YT 影片、Podcast...甚至實體策展)。
從這點來看,我認為「樣樣通,樣樣鬆」在 AI 時代其實是好事。
通,代表你有機會跨領域思考,連結遙遠的概念。
鬆,代表你不會被知識給綁死。
在很多個領域都建立淺淺的一點「手感」,會是讓你觸類旁通的底氣。
我在 2022 年 AI 爆發之前有試著學 Python(那時候想轉行當資料分析師)
後來真的太卡關了沒有堅持下去,但是我已經學完了基本的 HTTPS 概念、Git 版本控制、Python 虛擬環境架設、基本腳本語法、JS 腳本語法、CSS 跟 HTML 的概念。
這些都只是最基本最基本的東西——淺淺的一點「手感」。
現在 Vibe Coding 問世了,我發現要上手就非常快速。因為我已經知道怎樣看,甚至在 AI 即將出錯的時候,有一點點直覺可以聞出錯誤。
這樣就很夠用了。
偶爾三分鐘熱度一下,也是挺好的。
▋ 我們還有 AI
AI 的出現對於人類最大的幫助,也許就是幫助你克服「知識的詛咒」。
以我的案例,我是第一次在美國創立 LLC 並且要研究複雜的稅法,包含跨國報稅事務。
其實說穿了就只是「所以我到底要繳多少錢給誰」的這種簡單問題,會出現一堆:Form 1116、Permanent Establishment PE、FTC、IRS Publication 514、直接稅/間接稅、租稅協定、雙重課稅、S Corp、Solo 401k...
天啊,知識詛咒之高牆。
過去當然只能找一個熟悉跨國稅務的會計師,專門幫我解釋這些名詞,針對我的案例分析。
現在還是需要找一個會計師,但差別在於,我可以先用 AI 做功課,建立最基本的認知,然後帶著一個「很可能是錯的,但有基本概念」的想法去找會計師聊。
這仍然是大幅節省了我的時間(還有會計師諮詢的成本,一個小時 250 美金)。
▋ 好好利用 AI 的「平庸性」
除了讓 AI 幫我們解讀困難的材料,我認為還有一個特殊的用法。
我們可以善用 AI 的「平庸性」,來克服知識的詛咒。
大家都會說 AI 是「平均、平庸、大眾水平」,因為訓練語料是整個網路所有材料。
這完全正確,但是一般人的思考到這邊,頂多延伸到「所以拿 AI 來創作是不行的,品質會非常平庸」。
這也正確,《電馭寫作》課程的所有努力,都是在克服這個「平庸性」。
但重點是:你可以反過來利用 AI 的平庸,讓 AI 回來評估你的「內容」,給你「回饋」。
甚至「挑選」。
AI 的品味也是平均的水平。
AI 的品味,就是大眾的品味。
這代表:使用 AI 品味挑選出來的文章、材料、段落,有機會是直接符合大眾品味的文章。
AI 有機會幫助你,突破知識的詛咒。
這點是我最近的新發現,我還在摸索中,但我注意到的狀況是:
⇨ 1. 當我在處理一個很長的材料(例如 podcast 逐字稿),我常常直接問 AI:「材料裡面最有啟發性的重點是什麼?」
一開始完全只是偷懶。但後來我發現:這個問法,AI 會穩定產出很優秀的選題點,幾乎每次都會有讓我驚艷的內容。
我後來想想,這邏輯是順的:既然訓練的材料都是大眾水平,那模型對「什麼東西對我有啟發」的標準,自然就是大眾水平了。
⇨ 2. 當我用 AI 產出大量可以用的標題,並且請 AI 「直接選一個你認為最符合文章主體一致性的標題」,它挑選的結果,其實並不差。
這當然不只用在標題,也可以應用在選題、前言方向、文章風格、要呈現的重點....
這對高階的創作者非常有幫助。我一開始在設計 AI Agent 的時候,還很擔心 AI 的品味跟我差太遠,太平庸,會不會不好用。
後來發現:其實 AI 的品味平庸,反而因為可以代表大眾,作為一個重要的參考依據。
很多創作者的專業背景已經深厚,他最大的負擔不是知識缺乏,而是「知識詛咒」:他已經知道得太多,無法想像大眾的品味是什麼了。
如果你正在面對「知識的詛咒」,也許你可以多多利用「AI 的平庸性」 。
▋ 重點回顧
當你懂了一件事,你就很難想像「不懂」是什麼感覺,這就是「知識的詛咒」。就像敲節奏的人,腦中明明有旋律,但在聽眾耳裡,就只是一堆沒意義的敲擊聲。
知識的詛咒會搞爛你的定價策略:要嘛你會像那位工程師,因為太懂技術而高估價值;要嘛你會像我,因為太清楚自己的不足,反而嚴重低估了自己產品的價值。
要時時提醒自己:知識隨時會從「資產」變成「負債」。當你手上拿著錘子,你看什麼都會是釘子,這會讓你看不見事情的全貌。
寫作時的關鍵心法是:把讀者當成跟你一樣聰明,但只是剛好不懂你懂的東西。你要做的,就是把內容寫到「連你自己都覺得好像有點太簡單了」的地步。
永遠要記得舉例子,沒有例子的解釋,基本上就等於沒有解釋。不要用行話跟縮寫,如果你非用不可,一定要簡單說明那是什麼。
最有效的方法:找一個跟你目標受眾接近的普通人,請他在你面前看完。觀察他讀到哪裡皺眉頭、哪裡眼神發亮,你就知道答案了。
你可以反過來利用 AI 的「平庸性」。AI 的品味就是大眾的品味,讓它幫你挑重點、選標題,等於是直接請一位大眾品味的編輯,來幫你破解自己的知識詛咒。
大概這樣。
一不小心就寫了六千字,希望沒有太冗。
祝你一週順利。
PS:
文章中提到的 AI 使用技巧,都是我在《電馭寫作》課程的教學內容。
這門課是我近期的代表作,我的目標是幫助創作者,真正掌控 AI 的力量,成為 10x 產能電馭創作者。
我要讓每個創作者,都獲得屬於自己的一人寫手團隊。
《閱讀前哨站》瓦基:「聽起來有點不可思議,但它是真的:自從善用加恩在各個環節教學的題詞之後,我的寫作效率、寫作成效、寫作動機都大幅提升了!」
課程即將在 9/10 進入第二波銷售,銷售時間有限,請填表加入優先通知名單: https://forms.gle/8kBzTwC6He351yCe9
註一: Colin Camerer、George Loewenstein 和 Martin Weber 於 1989 年在《政治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發表的論文《經濟環境中的知識詛咒:一項實驗性分析》(The Curse of Knowledge in Economic Settings: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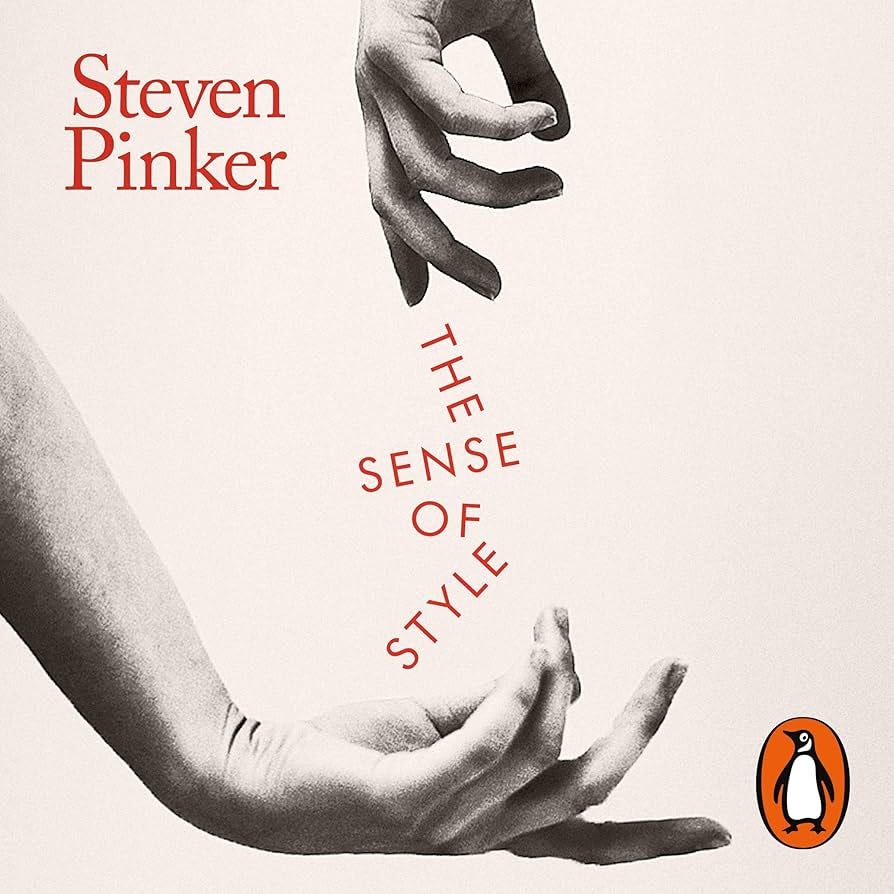

”但隨著筆記庫逐漸成長,我發現:把所有重點都記下來,這些知識反而是一種「負債」,不是「資產」。
因為當我選擇記下所有重點,注定有很多是我「無感」的筆記。
而這時候管理筆記盒,就是處理一堆我無感的資訊。那就變成是一個辛苦的工作了,而且我也不知道記得這些事要幹嘛——這些資訊對我沒有意義,那再怎樣看似重要,也只是雜訊。“
---
整理無感的筆記真的很痛苦,雖然我還沒有看開,但最近找到個方法,能減少這個情況。
我採用的方法是,看到有意思的內容,就用的電子閱讀器、readwise reader劃線。
真的對我未來有意義、會用得到的,馬上貼到筆記上。
這樣篩選後,既可以避免整理無感的筆記,
又因為有劃線了,減少了「不收集很可惜啊」的念頭,反而提升了讀書的速度。